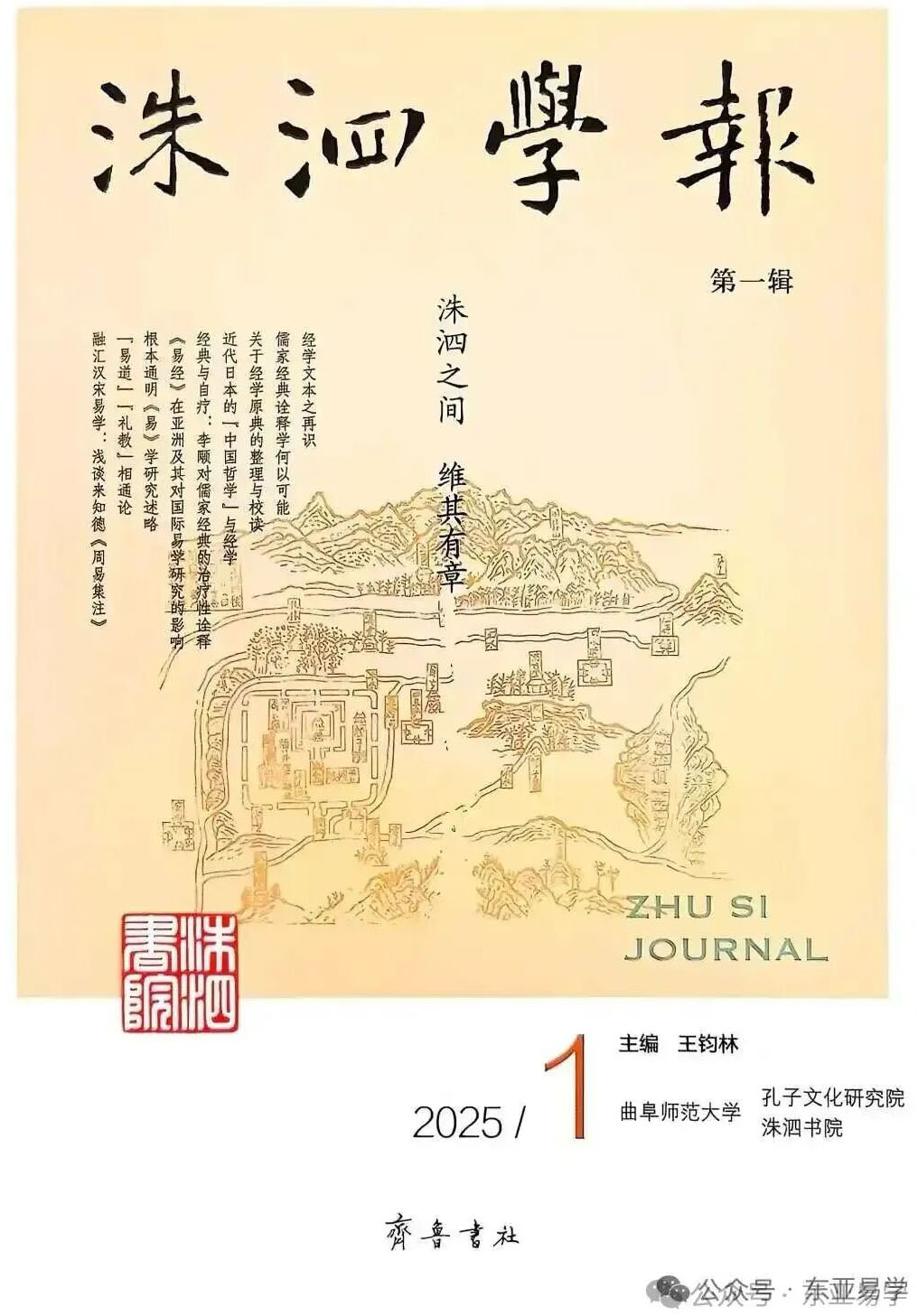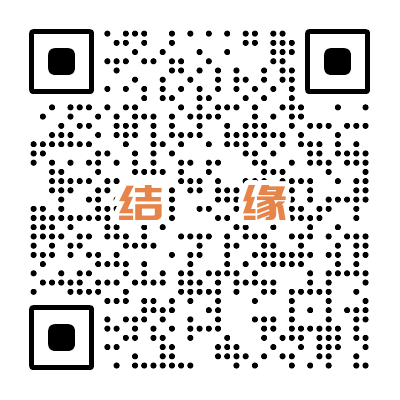吕祖谦易学兼顾理学与心学的特色及拓新
来源:王钧林主编:洙泗学报(第一辑),济南:齐鲁书社,2025年6月。
作者简介

张韶宇: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副教授,中国《周易》学会会员,国际易联会员。主要研究中国哲学,重点是易学及其与佛教、道教互动方面,偶涉地域性文化等。
主持地厅级以上项目7项,其中国家社科1项、省部级1项。参与市厅级以上项目10项,其中有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文化重大工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等3项。所主持贵州省领导圈示课题(2016年度)《贵州文化与旅游等宽领域深度融合发展研究》,荣获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年度项目三等奖。排名第三,林忠军张沛张韶宇等著《明代易学史》,荣获2016年度华东地区优秀古籍图书特等奖,(2018年07月22日)山东省第三十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省级)。
主要内容
摘 要
吕祖谦于易学颇有建树,一方面十分尊崇《程氏易传》,强调“以理绎经”,倡言天理正道的治《易》为学宗义,弘传理学派易学思想;另一方面又积极吸纳程颢与象山之说,释易为心,提揭“心卜”“心筮”之旨。此外,吕氏还极为注重易学、史学、事功之学等之间的互释与会通,从而强调《易》之经世致用的现实价值追溯。吕氏易学的这些诠释理念、方法及其所建构的理论学说,对后世易学及理学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
朱陆;理;心筮;以史证《易》
吕祖谦(1137—1181),南宋时期著名经学家、理学家、文献学家、易学家等,字伯恭,别名吕成公,世称“东莱先生”,婺州(今浙江省金华市)人。与朱熹、张栻并称“东南三贤”。《宋史》《宋元学案》皆有传。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吕祖谦发起和组织了中国学术史上著名的学术辩论会——“鹅湖之会”,但对朱陆之争并无偏袒,而是持论公允,兼容并蓄,各取其长,故而其学又与朱陆二家之学并立而呈鼎足之势。近年来,学界从哲学、经学、理学、实学、文献学等不同视角对吕氏之学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对吕氏易学也进行了积极剖析,取得了系列成果,理论见地也是各具特色和偏重。大抵而言,吕氏为学极为广博,不仅精于经学、史学、文献学、音韵学等,而且合理学、心学与事功之学等为一体,于易学则主张经传分离,力图恢复古《易》原貌,撰有《古周易》《古易音训》等。在解读《周易》时既广泛引征周程张杨等说,又发挥《程氏易传》之旨,强调以理释《易》,在为程朱理学易张目的同时阐发了自己的理学思想。同时,受程颢、象山之心性学浸润而注重熔融心与理,强调心为《易》本,倡言“心卜”“心筮”而兼具心学特质。此外,吕氏还特别注重以史实证诸《周易》经传文义,以《易》为经世致用之学,呈史事宗易学之理路色彩。由是,构建起自成一家之说的易学哲学体系。
一、天理正道:对程氏理学易的继承与发挥
吕祖谦易学思想深受二程学说的影响,对《伊川易传》尤其推崇,赞它“精深稳实”,“不可不朝夕讽阅”,“初学欲求义理,且看上蔡《语》《阃范》《伊川易》,研究推索,自有所见”。由是,“他(吕祖谦)在婺州刊印《伊川易传》,传播程颐的学说。所以,从吕希哲到吕祖谦,其思想无疑有二程学说的影响”。吕祖谦以程氏“理”或“天理”为其哲学根本范畴,认为“理”或“天理”即宇宙万事万物的总原则,而《五经》则是天下之理的载体,三圣作《易》更是阐释天下之“理”。他说:“二帝三王之《书》,羲、文、孔子之《易》,《礼》之仪章,《乐》之节奏,《春秋》之褒贬,皆所以形天下之理者也。”以《书》《易》《礼》等皆为“所以形天下之理者”,且强调扬弃汉唐“刳剔离析,雕缋疏鉴”的训诂式解经治学方法,倡导以“理”绎经和阐发五经“至理”。关于“理”或“天理”之义,吕祖谦还强调说“理,一而已矣”“大正者,理也”“礼,理也”。“天理则与乾坤周流而不息”, “循其天理,自然无妄”,“天地万物未尝不顺理而动也”, “理之在天下,犹元气之在万物也。……理之在天下,遇亲则为孝,遇君则为忠,遇兄弟则为友,遇朋友则为义,遇宗庙则为敬,遇军旅则为肃。随一事而得一名,名虽千万而理未尝不一也”。这样,“理”就被吕祖谦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存在于万物,又统辖了万物。于此,就吕氏所论“理”或“天理”内涵归纳而言:“理”或“天理”无所不在,天地万物同得此实然之理,万事万物虽殊异而于理未尝不一,天理即天命,既是天地万物都要遵循而不可违反悖逆的普遍原则和自然界的最高原则,具有永恒存在而不可灭的德性,也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体现为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及礼乐刑政制度等。不仅以理如同元气一般而为万物存在的根据和根本,且认为忠、孝等社会道德规范和礼乐刑政制度皆出于“理”或“天理”,皆是“理”或“天理”的表现形式。这就在天人合一观念的理论前提下,以天理或天道下化人道,以人道上附天理或天道,也就给“忠”“孝”等人伦礼乐制度披上了神圣的“天理”外衣。
由此出发,吕祖谦提出了天人无间的观点,认为人的言行举动,无非是顺从和按照“天理”“天意”“天道”办事,天人之间是相通合一的,一切莫大于“天”。人无论处于何种境况,无论顺逆向背,或取或舍,皆在“天”的范围之内,受“天”的约束和支配。他说:“抑不知天大无外,人或顺或违,或向或背,或取或舍,徒为纷纷,实未尝有出于天之外者也。顺中有天,违中有天;向中有天,背中有天;取中有天,舍中有天,果何适而非天耶? ……人言之发,即天理之发也;人心之悔,即天意之悔也;人事之修,即天道之修也。无动非天,而反谓无预于天,可不为大哀耶! ”“凡出于自然,而莫知其所以然者,天也。”以天大无外,故而“人言之发,即天理之发也;人心之悔,即天意之悔也;人事之修,即天道之修也”。吕祖谦又指出:“常人之济危难,必用私意小智以求济也。圣人则不然,顺天理之自然而已,汤、武是也。若涉难而不顺天意,是取败之道也。”揭示了同样是面对危难,常人与圣人之抉择截然不同,常人为能济危救难,常常出于一己之私而动用私意小智以求出困除难,结果往往因悖逆天意而致败。相反,圣人只是“顺天理之自然而已”,在强调天理自然无为属性的同时,也强调圣人亦要遵循自然无为之天理方能致吉。以程氏理学思想为根基,吕祖谦在解《易》时不仅盛赞伊川易学,而且积极发挥其理学易思想,认为“《伊川易》都不偏”。由此表明在以理释《易》方面,二者易学具有相通性,且在解《易》时多引诸程传以为征。在具体的解《易》过程中,吕祖谦不仅提出天道有复、至理无妄、顺天理之自然等思想,还通过象数以阐发义理思想,则与程氏易学忽视象数的思想有别,亦可谓是其在《程氏易传》基础上所作的拓新和发展。
正是基于对程氏理学哲学思想衣钵的传续,吕祖谦在治《易》中深受《程氏易传》影响而强调以理释《易》,提出“天下惟有一理”的命题,更以“理”对《周易》展开诠释而建构了一幅易学宇宙本体论和生成论的世界图式:“天下惟有一理。《坤》之《彖》止曰‘乃顺承天’‘德合无疆’而已。盖理未有在乾之外者也,故曰效法之谓《坤》。” 在强调“天下惟有一理”的同时,又释之曰“理未有在乾之外者”,故而坤之“德合无疆”乃在于顺承和效法皆依乾或理而运,由是乾坤相互依赖,对待激荡,不仅生成长育万物,而且彰显“乾理”即“天理”以德普及万物而无涯。虽然特重乾坤二卦,但吕祖谦也注意从《周易》他卦阐发“生生之谓易”的义理观,强调“读《易》,当观其生生不穷处”,以“生生不穷”之“理”来阐释《周易》,认为“天理”既是永恒遍在的又是生生不息活泼泼的存在体,万物生成之前即存在,万物既生之后则含藏并统摄于万物,万物消散泯灭后依然故我而不息止,“天地生生之理,元不曾消灭得尽,此《剥》之后所以必有《复》也”。同时,吕祖谦还指出至善的本体“天理”并非高不可攀、邈焉难求,而是切近生活而自然平易的日用伦常。他说:“大抵天下之理本无间,惟人自以私意小智限隔,如居小屋之中,未出藩篱墙壁,若才出得门外,便是大同。”“天下之理,既如渴饮饥食,昼作夜息,理甚明白,初无难知,惟人自见不明,往往求之至难不可卒晓之处,故多辛苦憔悴而无成。殊不知天下本无事,所以然者,以其不善推之故也,此之谓不受命。”尽管“天下之理本无间”,然在寻常人们往往由于自己“私意小智”或“私欲”的遮蔽而致使天理不彰,不仅不知天理自然无为感而遂通之律则,而且以私意汲汲以求“天理”终致“至难不可卒晓”,“多辛苦憔悴而无成”。相反,“天下之理,未有无感而应” , 一如渴饮饥食等日用寻常,其为理非常明白易晓,有感而应,惟在于人能够善推之而顺受之正。是以吕氏又言:“吾之性本与天地同其性,吾之体本与天地同其体。不知自贵,乃慕爵禄,不知一体之中自有广大之道。”以人本就与天地同一性体,只因舍近而求远,不知自珍自贵,自私钦慕富贵利禄而忘却“一体之中自有广大之道”。人们只要破除“私意小智”之藩篱限隔,经由“本心”自然,即可发见“有感而应”,也便可求而得悟“天理”。对此,吕祖谦又开示: “此理虽新新不息,然不曾离元来去处一步,此所谓‘立不易方’。”“盖是极正之理,增分毫则为赘,过分毫则为过。”以为极正之“理”虽新新不息,无有已时,然却未曾“离元来去处一步”,不仅完满自足,而且纯粹中正。既无增益和减损,又无过无不及;既无丝毫人欲夹杂其间,又无需费尽心机以求之。相反,若以本心自然之性即无为之“诚”和“无妄”体认“天理”,自然也就与“天理”一体无间无隔。这就以天理为充实着“极正”的完满的至善而成为世界万物的普适法则和人伦日用的根本准则,即《易》之“立不易方”。故而吕祖谦反复强调说:“盖无妄,天理也。才耕获、菑畬,则是有意作为,非天理也。”“至理之极,不可加一毫人伪于此,而犹有行焉,则乃妄而有眚矣。天理所在,损一毫则亏,增一毫则赘。无妄之极,天理纯全,虽加一毫不可矣。”以“人伪”即人欲,强调肆意而妄行必然招致灾眚。吕祖谦在《左氏博议》中还举“颍考叔还武姜”的历史事例进行了详细而生动的阐述:“盖庄公自绝天理,天理不绝庄公。一朝之忿,赫然勃然,若可以胜天。然忿戾之时,天理初无一毫之损也,特暂为血气所蔽耳。血气之忿,犹沟浍焉,朝而盈,夕而涸,而天理则与乾坤周流而不息也。忿心稍衰,爱亲之念油然自还而不能已。彼颍考叔特迎其欲还之端而发之耳。其于庄公之天理,初无一毫之增也。”显然,尽管人因喜怒之无常而遮蔽甚至自绝于天理,然天理本身则无丝毫增损,自始至终“与乾坤周流而不息”。
有类于朱熹“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万物中有太极”“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之说,吕祖谦亦认肯“理”与“太极”之关联,以“太极”即“理”即“道”;且在其著《易说》中借鉴程朱理学核心命题之 一的“理一分殊”说,阐释了其易学宇宙生成图式,把本体论与生成论统一起来,认 为“二而一者也” ,又“贯之以理,则一而已矣。……一而万,万而一者也”,认为绝对 之“理”藉由阴阳二气因缊激荡化育为具有形态各异的“万理”之物事。其间,“一理”没有任何的损伤,它不仅生成了对立统一的二物,而且还生成了丰富的世界万物。换 言之,千殊万别之万物万事虽形态各异,然皆有形上之“天理”统摄而一以贯之。吕 祖谦又指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非谓两仪既生之后无太极也,卦卦皆有太极;非特卦卦,事事物物皆有太极。乾元者,《乾》之太极也;坤元者,《坤》之太极也。一言一动,莫不有之。”“‘太极生两仪’,所谓理必有对待也,‘一阴一阳之谓道’;或问:‘范围天地’,伊川训为‘模量’,何也?曰:只缘天地无外。”释“太极生两仪”为“理必有对待”,即以太极为理;两仪即对待之阴阳。且以一阴一阳之道范围天地,为天地万物的普遍规律,认为“学者能玩味此语,则太极之妙可以默喻”。这样,卦 卦皆有太极,事事物物皆有太极,“太极”与“天理”也就自然而然地合二为一了。
天地间没有孤悬独立之“理”,诸如天地、阴阳、乾坤、高下、君臣、尊卑、夫妇等寻常事物,皆在“理”的含摄下而一体无间。吕祖谦说:“大抵天下之理,有进必有退,有荣必有辱。不待进极而后有退,当进之初,已有退之理;不待荣极而后有辱,当荣之初,已有辱之理。”强调“理”统摄下的天下万事万物既是相对而存在的,又是相互依赖而存在的,“有进必有退,有荣必有辱”,是为“天下之事常相对,有一病 则有一治法”。因而圣人强调“相反处乃是相治”,开示“皇皇汲汲,往求亲比”而不是封闭或孤立自己。但于相对而存在且地位和作用又不平衡的双方,或主导或被动,或施动或受动,吕祖谦强调以“诚”之“理”去交感,二者才能在相互因缊交感、激 荡共生中促使生成长育。他说:“君尊而臣卑,夫倡而妇和,上天下地,理之常也。然 下天而上地则为泰,男下女则为咸。盖以位言,则上下之分一定而不可易;以交感之 道言,则必在上者先感下,则在下者斯应。”故而尽管君尊臣卑、夫倡妇和、上天下地等为理之常态,此仅以位而言则上下之分一定而不可易;然而若以交感之道言,则必 在上者先感下,则在下者斯应之,故天下地上则为泰卦,男下女上则为咸卦。他又说: “若以势论之,则山、泽本不相资,山高泽深,固自为损;以气论之,则山、泽通气,本自有相资之理。”“天下之理,有通有塞,以诚相感,无所不通;一或不诚,则虽 近而一家,亦闭塞而不通。”以泽下山上损卦为例,认为损卦以势而论,则山泽本不相资,山高泽深,固自为损。但如果以气而论,则山泽通气,本自有相资之理。同时 以为,尽管天下之理有通畅有阻塞,但如果能够以诚相感应,自然会无所不通达。相 反,一旦有丝毫不诚,则虽近而为一家,也势必闭塞而不通。吕祖谦加以论证说:“大凡随,虽小随大,柔随刚,阴随阳,下随上,必是上有以先之。天下之理,未有无感 而应,故刚来而下柔,然后柔动而悦,如尧、舜之圣,只是舍己从人。必须我有可随 之道,然后能使人随我。”强调随卦虽以“小随大,柔随刚,阴随阳,下随上”为随 之“理”,然在“上”者“只是舍己从人”而率先去感“下”,惟在我需“有可随之道”即以“诚”之“理”感人,然后才能使人随我,别人也才能够心悦诚服地随我。
颇具特色的是,吕祖谦还强调通过象数来阐发《易》之理,这就有异于《程氏易传》重义理而忽象数的为学理路。他说:“‘恒’之一字最难看,可以见六十四卦之妙;非独可以见六十四卦之妙,又可以见《易》之全体。盖乾、坤者,《易》之门也。外乾故刚上,内坤故柔下。雷动而风发,此相应常久之道,故《恒》云:‘巽而动。’初与四为应,二与五为应,三与上为应,皆以刚柔相应而为《恒》。晓此四字,则六十四卦皆具见矣。‘刚上柔下’,乃尊卑定分之常;‘雷风相与’,乃运用变化之恒。‘巽而动’者,天地万物未尝不顺理而动也;‘刚柔相应’,天下之理未尝无对也。此四者,乃天 地之常经,大《易》之正义也。”以恒卦之象数来阐发其义理,认为通过恒卦不仅可以 窥见《周易》六十四卦之妙,甚至可以透视《易》之全体,而恒卦诸爻之间的象数关系 则体现了易道恒常、“刚柔相应”、“尊卑定分”、“顺理而动”等天地之常经。在吕祖谦 看来,恒卦巽风下震雷上,故下阴柔而上阳刚,刚柔相应而为恒,初六与九四、九二 与六五、九三与上六等一一为应,不仅体现了尊卑定分之常,而且雷风相与而动还体 现了运用变化之规律,乃至天地万物未尝不顺理而动以及天下之理未尝无对的道理, “此四者,乃天地之常经,大《易》之正义也”。吕祖谦又推而广之加以发挥,判定该原则亦体现在《周易》六十四卦之中,具有普适性。这就基于恒卦天地恒久之道,即 刚柔相应之则,推阐衍化为《周易》六十四卦所具之普遍规律。故而吕氏又谓:“大抵通天下万世常行而无弊者,必正理也。若一时之所尚,一人之所行,则必不能久,故 恒之亨,利于贞。亦如汉文帝好黄、老,至文帝之后则黄、老之道不行。梁武帝好浮 图,至武帝之后则浮图之道不行。盖非正道,则必不能久也。‘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 也’,‘不已’两字最要玩味。天穹然在上,使其无不已之道,则久而必坠;地颓然在 下,使其无不已之道,则久而必陷。惟是有不已之道方能久。”以为贯通天下万世常行 而无弊端者,必然是恒久不已之道的正理正道,而恒卦恰是这一原则的完备体现。反 之,若非正道,则必然不能够持久永固。是以吕氏特别拈出“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之“不已”二字,且以此为恒卦所具有的恒久之道的根本理则。由此,吕祖谦以“理”为据对《周易》展开诠释,以“至善”之“天理”为宇宙本源和本体,建构了一幅恒久 不已又品类多彩的世界图式,强调唯有坚守“正理”“正道”方能获恒久之道而不致有弊,如是也才能够彻悟《周易》“生生不已”之真谛所在。
二、心卜心筮:对象山心学易的认肯和拓展
对于多数宋明理学家而言,他们分别或以“理”或以“气”或以“心”等为本体来建构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然吕祖谦却不同,他在继承二程理学基础上又与朱子积极互动,认肯其理或天理诸说;同时于象山之心学由欣赏至交互而亲近,戚戚焉而向往之,认为“心外有道,非心也;道外有心,非道也”,实则以心与道为不二法门,以心与理相即不离,从而熔铸程朱理学与陆氏心学于一体,可谓兼顾理学与心学,带有十分鲜明的调和朱陆的印记。在程朱理学思想体系中,作为“形而上者”的“道”或“理”,二者同质而为超越物质之上的本体,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和根源。吕祖谦以心与道不二为说,强调心与理为一,不仅突出“心”之地位,而且以“心”与“理”或“道”相同一。很显然,吕氏此论实与程颢心性思想及象山“道未有外乎其心者”一说有同工之妙。众所周知,象山素以“心”与“道”或“理”为同一概念,直接视“心”为宇宙本体。同样,吕祖谦亦强调“心”之功用和世界本源义,既以“理”或“天理”为其哲学最高范畴而成就宇宙万物的总原则,又强调以“心”与“理”相同一即“心 理不二”。这可以说既是对二程理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象山学说的推衍和发 挥,融理学与心学于一炉。潘富恩说:“他(吕祖谦)既认为‘理’或者‘天理’是世 界的本原,又规定‘心’总摄万物,而使自己的哲学具有两个最高范畴。”吕祖谦还立足于天人无间的哲学基本观念,认为天命和人心相通。他说:“圣人之心即天之心,圣人之所推即天所命也,故舜之命禹,天之历数已在汝躬矣。舜谓禹德之懋如此,绩之丕如此。此心此理盖纯于天也。”开示“圣人之心”即“天之心”,实则以圣人即 天。这里所谓“圣人”是指能移易客观世界的圣者,即“圣人之所推即天所命”,从而 区别于通常意义上所谓的“凡人”。又以“圣人之心”不仅是“天心之享”乃至“天命 之系”,而且还是“与万民之心如一”之“公心”。且谓之:“盖天心之享者,天命之系 也。”“圣贤之心,与万民之心如一,则公心也。公者,天之心也。汤之时,民心既 然,而伊尹又与之同心,则天心可见矣。”由此圣人之“本心”备万物于一身,没 有内外,本自具足,完整无缺,“万物皆备于我,万理皆备于心。……天下之理皆具于吾心之中”。无论是“天命”抑或是“理”或“道”,其实都与“心”一样,是具有绝对普遍性而无所不在的存在体。换言之,以“心”即“天”即“理”即“道”。如 是则“心”“性”“理”“天”等就被沟通熔铸起来而变成周延同一的概念,乃至论及“心”“理”“气”“性”“太极”“道”等诸范畴之相互关联时,更是彼此难分而混一。从表面看,吕氏试图调和理学与心学两派分歧而呈现折中之色彩,实则是对宋儒理论分歧的一种融会贯通,这也为明代阳明心学的集大成提供了一种学理借鉴。
植根于天人相感无间的理论基础上,又融贯理学与心学为一体,以“心”与“理”同一而成为世界本体,由此吕祖谦在以理释《易》的同时也赞成以“心学”诠《易》,认为《易》或易理与人心不容有二,主张以“心学”的视角去审视《周易》,提揭 “《易》者,圣人洗心退藏之书也”。他说:“圣人备万物于我,上下四方之宇,古往今来之宙,聚散惨舒,吉凶哀乐,犹疾痛疴痒之于吾身,触之即觉,干之即知。清明在 躬,志气如神;嗜欲将至,有开必先。仰而观之,荣光德星,欃枪枉矢,皆吾心之发 见也;俯而视之,醴泉瑞石,川沸木鸣,亦吾心之发见也;玩而占之,方功义弓,老 少奇耦,亦吾心之发见也。”以圣人等同于宇宙天地,天地万事万物备具于圣人一身,圣人之身、圣人之心与天地万事万物浑然一体。无论是天地宇宙之变迁,亦或是万事 万物变动不居之“聚散惨舒”“吉凶哀乐”等,圣人无不“触之即觉,干之即知”。同样的,无论仰观俯察,还是“玩而占之”,乃至“老少奇耦”等,也无不是“吾心之发 见”,俨然以“心”为本而生养化育万事万物。这一理念不仅体现在他于《易说》中以 “心学”的理路诠释了某些卦爻辞,更体现在他以“心学”理路视角阐述了对卜筮的基本看法:卜筮不是“人心”在作祟,而是“本心”的自然流露,即以卜为心卜,筮为 心筮,以《周易》之变占卜筮等为本心之变占卜筮。此说可谓是一种创建,也可以说 是对《周易》之卜筮一说的全新解读。他说:“未灼之前,三兆已具;未揲之前,三易 已彰。龟既灼矣,蓍既揲矣,是兆之吉,乃吾心之吉;是易之变,乃吾心之变。心问 心答,心叩心酬,名为龟卜,实为心卜;名为蓍筮,实为心筮……蓍龟之心,即圣人 之心也。”“是心之外,岂复有所谓蓍龟者耶!噫!桑林之见,妄也;偻句之应,僭也;台骀、实沈之祟,妖也:彼蓍龟之中,曷尝真有是耶?妄者见其妄,僭者见其僭,妖 者见其妖,皆心之所自发见耳。蓍龟者,心之影也。小大修短,咸其自取。”一方面强调“未灼之前,三兆已具;未揲之前,三易已彰”之说,另一方面又以人事之吉凶 祸福皆决定于一心。卜筮,实质是卜之于一心,“名为龟卜,实为心卜;名为蓍筮,实 为心筮”,究竟言之,皆圣人之“心”的作用和符示,不仅不存在心外之蓍龟者,而且所谓“桑林之见”“偻句之应”“台骀、实沈之祟”,凡此等等,实则“皆心之所自发见 耳”。因而,吕祖谦自然地得出结论:“蓍龟之心,即圣人之心也。”“蓍龟者,心之影 也。”关于“占卜”,吕祖谦又说:“未占之先,自断于心,而后命于元龟。我志既先定 矣,以次而谋之人,谋之鬼,谋之卜筮。圣人占卜,非泛然无主于中,委占卜以为定 论也。……其所以谋之幽明者,参之以为证验耳。……心者,神明之舍。”这里,“心”之主宰义十分清楚,所谓“未占之先,自断于心”,卜筮只不过是“参之以为证验耳”。于此亦可看到,吕氏在调和兼容理学与心学两派的观点过程中明显有偏向“心学”的 迹象。
与《易》之“心卜”一说紧密相关联,吕祖谦还十分注重“明善”“复善”功夫以复归人之良善本心,亦即天道或天理之复,由此成就儒家所孜孜以求的“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之境界。这可以说是其对《易》之为“圣人洗心退藏之书”界说的另一注释。在吕祖谦看来,“人能于善心发处,以身反观之,便见得天地之心”,由“见得天地之心”而达至天理昭彰之境。他说:“夫《复》,自大言之,则天道阴阳消长,有必复之理;自小言之,则人之一心善端发见,虽穷凶极恶之人,此善端亦未尝不复,才复便有亨通之理。且以卦体之爻观之,初九一阳潜伏于五阴之下,虽五阴积累在上,而一阳既动,便觉五阴已自有消散披靡气象。人有千过万恶,丛萃一身,人之善心一复,则虽有千过万恶,亦便觉有消散披靡气象。”可以看出,吕祖谦极为重视天道之有复的功夫论,不仅论及“天道阴阳消长,有必复之理”,而且开示“人之一心善端发见,亦未尝不复”。在他看来,天虽以无心而发用,然在人却以私意障蔽之。不过,尽管人以私意障蔽天理和良善本心,然却于庶类之秉彝终究不可泯没断绝,如是天理和良善本心之运行也就无有间断和阻隔。因而学者最紧要处就是于“天行”即“人之善心发处”上用功,不仅可恢复本初天行自然之道,亦促使人心善端固有之理得以彰明。吕祖谦于此所论不仅将孟子性善论和《周易》“剥”“复”卦义相结合,强调“人之一心善端发见,虽穷凶极恶之人,此善端亦未尝不复”之教,而且又着实与后之阳明先生所倡导“致良知”之教语脉贯通而旨趣相侔。故而吕氏以“学者须是心不外缘”释《易》之“君子学以聚之”,乃至强调从尧舜到孔子,圣贤们相承不断的亦不过是“明善”之功,于“明善”之外,更无所加其损益。在吕祖谦看来,人生下来就有“善端”,虽然“天理”有时被私欲所蔽,但只要“人之一心善端发见”,“于善心发处,以身反观之”,私欲剥落净尽,是谓“自存本心”,“天理”亦最终必复;虽穷凶极恶之人,也能改恶从善。如是则“人之善心一复”与“天道之有复”相同一,自然就达至“内外一体”之境界,也促使其易学功夫论回归到天理和良善本心的终极关怀上来。
吕祖谦还以“心学”为据对《周易》众多卦爻辞进行诠释,并以此来阐发其具有“心学”特质的易学思想。其中,在解履卦初九爻时,他说:“人当件件守初心,如自贫贱而之富贵,不可以富贵移其所履。惟‘素履’,故‘无咎’,盖不为地位所移也。此最是教人出门第一步。”告诫人们要于事事物物谨遵恪守己之“本心”,虽遭遇非常之变而不迁不移,毫不动摇,强调人们无论是贫贱还是富贵,无论卑下还是高贵,无论身份如何变易,都要持之以恒、善始善终地守持住“本心”,不忘根本,且以此作为教人出门的首要法则。吕氏此说显然是对孟子“大丈夫”和“四端之心”说的继承发挥。在解释豫卦《大象传》时,吕祖谦以为先王体诸豫卦“顺动之象”而作乐,然就其本原意义言“乐者,亦本诸人心”,推而广之又寓诸金石钟鼓之间。因是若洞晓豫卦雷之所自发处及乐之所自起处,则豫之义自然而然可明。在解蛊卦“巽而止”一节时,吕祖谦认可传统《易》之蛊卦巽下艮上及巽有顺和艮有止义,同时又指出“巽而止”具有普适性,巽顺曲折而中又有所主,虽确然而不可变,但亦不逆于人心,如是则所事为自然顺遂达成。相反,如果内里既无所主,外又只止而不巽顺,不仅缺失“巽以出之之道”,亦且存有“拂人心处”之忧,其事为之不治自然无疑。在解复卦《象传》时,吕祖谦以“固有之良心”喻复卦初九之一阳,示人以天理或天地之心不可断灭而永恒存在。一旦机缘具足,善心发用,善端自然生发,曾经被遮蔽之天理或天地之心或固有之良心势必复初而昭彰。由此复卦所蕴之义也就得以揭示。在解大畜卦《大象传》时,吕祖谦以人方寸大之“心”可以存纳编简所存千古之上解释之,以人方寸大之“心”可以留藏八荒之间衍义之。此论与象山“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之旨可谓同趣。自然的,大畜卦之以山畜天、天在山中也就顺乎理了。其他如“‘履霜坚冰,盖言顺 也’,此一句尤可警。非心邪念,不可顺养将去。顺养去时,直至弑父与君。如饮酒,初时一两杯,顺而不止,必至沉湎杀身。……今世俗所谓纵性者,即顺之谓也。……‘君 子以惩忿窒欲’,不顺之之谓也。大抵非心邪念,若顺将去,何所不至?惩治遏绝,正要人著力”等诸说,不一而足,皆可视为吕祖谦以心诠《易》的典型义例。而吕祖谦不仅以人之善心与天道比附同视,且以天行自然之道与人心固有之理等量齐观,都具 有遍在、生生、自然等根本特性;且以易之生生为初始点,以阴阳、乾坤等基本运行 理则寓于一切事物中,建构了一多相即的本体哲学。这一构造在事实以及价值层面上 化解了善恶来源和标准问题上的抵牾,又在心理为一的本原良善性基础上为个体修为 指出了为善去恶的功夫路径。很显然,这是“博学多识”的吕氏力避他者“学之所短”,而积极汲取其“学之所长”的治学实践的精深结晶,也是他广泛与各学人深入、潜心 交往的优异成果,既成为了其融会理学与心学于一体的滥觞,也展现了其虽“博杂”而又具有一定开拓创新的学术品格。
三、经世致用:对史事之学的推崇和阐扬
除了受理学和心学的影响,吕祖谦还深受其家学及事功学派史事易学思想等影响,且十分崇尚《左传》《史记》《汉书》等史学著述并重视经世致用的事功之学,强调引史证经,注重引史证《易》以明道或阐理。吕祖谦注重研究历史,目的是要从历史中取得经验教训和借鉴,从而洞晓历史发展变迁之缘由及其规律。他说:“读史先看统体,合一代纲纪风俗消长治乱观之。”认为读史不可随其成败论是非,也不能轻易出议论而草率立意见,而须揆之以理等。又强调“看史非欲闻见该博,正是要‘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了解史事的本末源流和成败的前因后果,以资借鉴,不仅有助于身心德性提升和完善,而且于拨乱反正修齐治平等亦有助益,即其所谓“大抵事只有成己、成物两件”。这种“观其所变”的历史观察方法,正是他遥宗太史公之学的结果,是对史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而“通古今之变”历史观的继承和推衍,也是他藉以证诸《周易》的有力举措。
《周易》作为五经之首,大道之源,是治国理政、济世救民之权舆,更是以史绎经典型例证,其滥觞于《易传》易例,内里即有以文王、箕子等史迹诠释《易经》卦爻辞之例。之后,历代的易学家在诠释《周易》这部经典时,几乎都绕不开这种解读方式,而四库“两派六宗”之史事即其重要易例之一。吕祖谦更是得心应手地运用了这一解《易》方式,其引史证《易》固然会使得《易》变得驳杂,但亦可以使《易》真正地成为“经世致用”之学。基于此,吕祖谦强调以史解《易》,并于《易说》开篇即说: “‘乾:元,亨,利,贞。’如尧,‘钦明文思’为尧;舜,‘浚哲文明’为舜。”以远古圣王尧“钦明文思”、舜“浚哲文明”之德诠释乾卦“元、亨、利、贞”四德,藉史例以阐发其义理易学,强调应以“德性”“王道”等理性工具为治国基本方略。
其他方面,如在解泰卦初九爻时,吕祖谦说:“当泰之初,贤人汇征,人君不能遍 识,必首先用一大贤,则天下之贤人自然牵连而进。如舜之选于众,举皋陶,则八元、八凯皆进;汤选于众,举伊尹,则旁招俊乂,如仲虺之徒皆进。”以舜、汤用人为例,旨在说明天下贤人以其同类而行之道理,君主只需任用一个大贤,则天下贤人自然就 会相互牵引而共进。在解泰卦九二爻时, 吕祖谦认为处泰卦九二爻之时,因“包荒”而使得“朋亡”,且以汉唐两朝在“乱世”和“治世”之时“朋党”之状为例加以说明,指出处乱世时人们无暇结为朋党而蝇营狗苟,而处安泰时则人们往往拉帮结派而弄权 营私。在解谦卦六四爻时,吕祖谦以谦卦之六四爻处大臣之位,乃多惧而危难之地,上有六五谦顺之君,下有九三劳谦之臣,于此境遇下圣人但教授世人应以“为谦”处 之而广施谦德。不然,则如西汉时杨敞、车千秋辈尸位素餐,德不配位,能不胜任,缺乏主见和担当,结果只能祸乱国家黎民。在解随卦九四爻时,吕祖谦说:“九四,天下皆随于己,当危疑之地,虽正亦凶。惟至诚于道,自然无咎。所以至诚无咎者,为其自诚而明故也。 ……然又如燕之慕容恪,亦当主少国危之时,内有强臣,外有强 宗,惟慕容恪能以至诚自守,故能全燕之社稷,而无纤毫之咎,正得‘有孚在道’一爻之象。”认为随卦九四爻尽管在随之际而天下皆随于己,然而处当危疑之地,虽正亦凶,何况九四爻以阳居阴位而不当,其咎自然可知。不过赖于九四爻一心惟至诚于道,虽位不当,自然亦得无咎。而其之所以至诚无咎者,乃在于“为其自诚而明故也”。且举前燕慕容恪为例以明之。恪之所处时位有似随之九四爻,然能以至诚之道自守辅主,不仅获保全燕社稷之功,而且自身亦无丝毫过咎。
此外,在诠释离、解、蛊、临、大畜等卦时,吕祖谦均以历史事件和事实去解说其卦爻辞,通过经史互参以阐释其中所蕴含的治世道理和原则。一方面注重从历史视角诠释艰涩难懂的《周易》卦爻辞,以经史与《易》互证互诠,以清晰晓畅的史实彰显《易》之“广大精微”“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易道易理,使得易学诠释理路多元化;另一方面依凭历史的经验教训,借古讽今,试图促使当政者借史鉴今,以《易》中之史和圣人之道为鉴而益于安邦治国,着力于经世致用,内里无不充溢着对史事易学以及事功学派的推崇和阐扬。
结 语
《宋史》曰:“祖谦学以关、洛为宗,而旁稽载籍,不见涯涘。”是以吕祖谦为学不拘一格,既以理或天理为世界本原,又规定本心总摄天地万事万物。然惜天不假年月,吕氏未及将“心学”“理学”“事功之学”“气学”等完全熔铸为一体,其学术思想和成就虽广博而宏阔,却又显得不够凝练,缺乏系统严整性。这可能是《宋史》将其列入《儒林传》而未入《道学传》的因素之一。故而《宋元学案》云:“小东莱之学,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化其偏,宰相之量也。惜其早卒,晦翁遂日与人苦争,并诋及婺学。而《宋史》之陋,遂抑之于《儒林》。然后世之君子终不以为然也。”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吕氏对易学古文献的整理疏解取得了优异成果,在教授后学时对易学解读传布产生了积极的历史影响。吕祖谦易学以经传相分、通过象数阐发义理为特征,对朱熹易学产生一定的影响;其有关治《易》、编纂《近思录》、撰写《伊洛渊源录》等,在朱熹新理学的创立中亦有一定襄助之功;吕氏《古周易》更是朱子撰《周易本义》时采用的底本,其音训也是径用吕祖谦的成果。而在治《易》具体活动中,吕祖谦提出“天下惟有一理”的思想,以天理、正道解《易》,又注重以象数阐发义理,与程颐易学具有相同相异之处。甚至弥补了朱熹独崇理学之局限,吕祖谦调和了理学与心学分歧,并认可陆九渊心学理念,强调人心与易理不二,心外无道,道外无心。至于其据永康、永嘉学派诸学者经世致用思想,以易学与史事相互诠释,将易学与现实问题相结合,强调经史互证,对匡正世道人心有所助益。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吕祖谦为学不名一家、不主一说的博大宏阔特色。同时,吕祖谦还在治《易》中娴熟地运用易例“承”“乘”“比”“应”及易象、卦变等,发挥《易》之“中”“正”“时”“位”“卦主”等传统解《易》体例,强调知晓“刚柔相应”则《易》之“六十四卦皆具见矣”,甚至依于“《易》不可为典要”而提出“《易》之爻,大抵随步换形”一说以诠释《易》之卦爻辞。又结合当时社会历史的实际而进行了深切的思考,尤其对易学中的辩证思维颇有自己的切身体会和发挥,对处于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各卦爻之变易的理解,不拘泥于一义,深契易道“唯变所适”之旨。所有这些说明吕祖谦易学不仅没有固执于一成不变的通行全经的诠释体例,而且意欲突破汉唐诸儒的解《易》路数,试图在义理指导下对《周易》卦爻开出全新的诠释理路。
但也应看到,由于立足于对世界或哲学基本问题的认知和回答的不同,又因受家学浸润、释道之风及时代思潮风尚和个人际会造化等影响,吕祖谦的学问包括易学不仅显得有些“博杂”,而且其为学也时有突破正宗理学的倾向,甚或有时道释之学等亦杂于其《易》著间,如其谓:“释氏之湛然不动,道家之精神专一,亦近于‘有孚’,只为非‘在道以明’。”即以佛家之“湛然不动”及道家之“精神专一”诠释《易》之“有孚”,以三者为一。这是我们在解读吕氏易学时需要批判审视的。
文章来源
《洙泗学报》
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