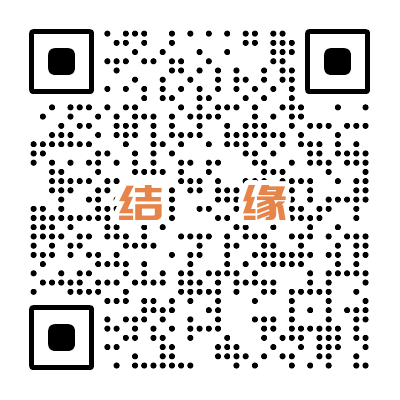易经》在亚洲及其对国际易学研究的影响
李伟荣 | 《易经》在亚洲及其对国际易学研究的影响
来源:《洙泗学报》第一辑。
作者简介
李伟荣,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和博士后合作导师,“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成员,主要从事思想文化史、中外文化交流史和比较文学等的教学研究工作。出版过《英语世界的<易经>研究》《翻译、传播与域外影响——中国典籍翻译与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研究》《英语世界易学研究论稿》等专著。
主要内容
摘要
《易经》问世后,尤其是在汉代成为“五经之首”,向东(或东北)传至近邻如朝鲜半岛和日本,向南则传至近邻越南,然后再向外传播。尽管如此,20 世纪中叶以前,《易经》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依然不大。20 世纪中叶以后,由于有了吴伟明、司马富和范多思等熟谙英语并积极用英语进行著述的易学家的努力,《易经》经由日韩越和其他亚洲国家传播到了欧美诸国,对这些国家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甚至隐隐形成了国际易学研究的雏形。
关键词
《易经》;亚洲;东亚易学;世界性意义;国际易学研究
早在《汉书 ·艺文志》中就有记载,《易经》为“群经之首” , 它与《诗经》《尚书》 《礼记》《春秋》共同构成“五经”。如果加上佚失的《乐记》,则称“六经”。后世学者多对此存在质疑。自欧阳修始疑《易传》作者非孔子,经过崔述、康有为等人推波助澜,质疑声浪在 20 世纪前半叶的疑古运动中达到顶峰;近年来学者们又重新肯定《易传》与孔子之关系,但目前对《易传》作者的考辨尚无令人信服的答案。《易传》包括《彖传》《象传》《系辞传》《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七种,其中,前三种各分为上、下篇,与后四种加起来共十篇,故称“十翼”。再加上《周易》分上、下经,故《汉书 ·艺文志》称其为“《易经》十二篇”
《易经》的对外传播,与《论语》的对外传播,不管是在时间上还是机制上,都非常类似。同样的,《易经》问世后,尤其是在汉代成为“五经之首”,向东(或东北)传至近邻如朝鲜半岛和日本,向南则传至近邻越南,然后再向外传播。杨宏声、吴伟明和陈威瑨等均涉足过东亚易学的研究,但许多问题仍有待深入思考和探讨,如现有研究更多着眼于东亚诸国易学比较,而对东亚易学宏观问题的研究过于简略。林忠军曾指出,东亚易学,自古迄今,不是中国易学的复制翻版和东亚诸国易学之简单组合,而是起源于中国、在他国传播之后,不断展现其发展的同步与连续性、思想与方法的相似性及其思想本土化的易学;而且随着国际性的学术交流互动,当今东亚易学个性化、本土化特征越来越不明显,东亚诸国易学交叉研究新格局已经形成,一体化特征日益凸显。
到了 16 世纪,随着欧洲传教士入华,《易经》也由他们带回欧洲(一方面是《易经》经籍,另一方面是他们的翻译),再从欧洲传播至美洲等其他各洲。2004 年,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纷纷建立,并培养了更多汉语专才,《易经》也就完全传播到全世界,逐渐成为世界经典之一而流传于世。
我在《域外〈论语〉传》一文中曾经说过:“一部书就像一个人,在其传播过程中有着各种各样的故事。” 《易经》在域外的传播也不例外。与《论语》相似,《易经》的对外传播路径最开始大致也分为南北两路:南路从中原传至岭南,再经岭南传至越南和东南亚等地;北路从中原传至东北,再经东北传至朝鲜半岛和日本。
《易经》传播到亚洲儒家文化圈内的日本、朝鲜、韩国和越南以及新加坡等其他亚洲国家,时间都很早。因为这些国家与中国发生联系或关系的方式并不完全一样,所以《易经》等儒学经籍和价值观在这些国家的传播,其方式也不尽相同。主要原因是日本、朝鲜、韩国和越南与中国都是近邻,或是一衣带水,或是国土接壤,早期都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一开始也同样使用汉字,直到他们有了自己的文字后,汉字才在他们国家逐渐少用甚或不用;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亚洲其他诸国由于大批华人迁入,包括《易经》在内的儒家经籍和价值观也开始传播 。可见,不管采用什么方式传播,《易经》无疑都是传入这些国家的最重要的经籍之一。
美国著名清史专家、易学家司马富(Richard J.Smith)指出,《易经》传播到东亚各国的具体情况尽管不同,其传播方式却似乎有一些相似之处。第一,从这些国家的建国早期到 19 世纪末,就像在学术界西方人使用通用语拉丁语一样,朝鲜、韩国、日本和越南诸国几乎所有精英的通用语言都是汉语的文言文,因此无需翻译。当然如果要让更多的普通人更容易理解,则要将它翻译成口语化形式。第二,在同一时期,中国的儒释道思想广泛而不断发展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这三个领域智识阶层的生活,也同样影响了东亚这几个国家的智识阶层。第三,《易经》在中国维持了两千多年的崇高地位,进入 20 世纪,它在东亚这几个国家也从未缺乏影响。第四,东亚各国借鉴中国文化的方式是他们定期派遣使者(例如隋唐时代的遣隋使、遣唐使等)访问中国,回国时他们以个人或团体的方式将中国经籍和传统以自觉且相当系统的方式带回自己的祖国。一旦我们的经籍抵达这些国家,它们便与本土思想和机构产生互动,进而产生出显著差异的、与《易经》息息相关的知识生产。
一、《易经》在朝鲜半岛
众所周知,韩国的国旗为太极旗,其寓意体现了中国的《周易》思想,中央的太极象征宇宙:蓝色为阴,红色为阳;4 个角落是 4 个经卦,左上为乾,右下为坤,右上为坎,左下为离,分别代表天、地、水、火。
刘正指出,《易经》在东亚的传播起于古代朝鲜半岛,再由朝鲜半岛传到日本。 以《易经》等“五经”为代表的中国儒学何时、如何传入朝鲜半岛?现任韩国学术院正会员(院士)、高丽大学终身教授、韩国孔子学会会长尹丝淳认为,中国人大幅移居朝鲜半岛始于战国末年(前 246—前 240),随之《易经》等儒家经籍得以传入,儒学也自然传入了朝鲜半岛。有趣的是,佛、道传入朝鲜半岛,朝鲜三国时期各个朝代都有正式传入的记录,唯独儒学的传入没有记录。在高句丽时期,佛、道首先经由僧侣或个别知识人引入,后来从国家层面正式引入,这都有明确的记载。与佛、道相比,儒学似乎是民间自然传入的。儒学思想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之后,才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进而从国家层面采取积极的吸收和引用措施(比如太学的建立等)。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日本的儒学始于韩国儒学的传授。早在公元 3 世纪至 4 世纪,百济的王仁就尝试将儒家经籍如《易经》《论语》传到日本,并教授日本太子;同时期百济的阿直歧和辰孙等,也来到日本担负起教育日本太子的任务。
与日本类似,由于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和超越性,朝鲜半岛也有人来到中国留学,学习《易经》等中国儒学经籍。渡唐留学有自费的,也有通过外交渠道来的“宿卫学生”。这种情况在唐朝达到鼎盛,据统计,仅在 821 年就有 58 名学生通过了唐朝的宾贡科考试,如金云卿、金叔贞、崔志远等。《易经》等儒家经籍在朝鲜半岛的广泛传播,有多方面的因素。一是与这些国家的开科取士有关。科举分几类,主要有进士科、明经科、医科和卜科。明经科主要考察参试者对一些经籍相关内容的掌握程度,因此主要从《易经》等“五经”中出题。 二是“殿阁讲论”的举行。睿宗在 1116 年设立了“清燕阁”和“宝文阁”。宫廷中的这些殿阁主要用于保管书籍,同时也设立直属官员来诠解《易经》等儒学经籍或《贞观政要》等政治书籍。也就是说,这些殿阁的功能就是供学者官员专心研究儒学经籍而准备的,同时也让高级官员在此做研究报告。在清燕阁等殿阁中举行的“讲论”,是由王直接主管的。那个时代所有的代表性儒学学者都参与了“殿阁讲论”,讲论经籍的次数有 40 多次(其中睿宗时期 24 次,仁宗时期 15次),讲论使用的书籍主要是《易经》等经籍。从使用频率上看:首先,使用最频繁的是《书经》,因为这利于官员们了解儒学中相关政治思想和实践事例;其次,使用《易经》比较多的是当时的王和学者,他们比较关心融合了伦理和政治的基础哲学,并且多探索政治和政治的伦理间的关系和政治的伦理证据。
《易经》在朝鲜半岛产生更深入的影响始自朝鲜王朝的建立。1392 年,朝鲜王朝成立,排斥高丽王朝的国教佛教,而奉程朱性理学为统治思想。最初引进朱熹性理学的学者是安珦。安珦弟子中排第一的当属禹倬。禹倬的易学造诣很高,程颐的《易传》刚刚传入时,在谁都没有能力解释的情况下,他潜心研究一个多月就率先解读了《易传》,并将其传授给学生。下一代学者中,李齐贤最具代表性。他是安珦弟子权溥的女婿,也是安珦弟子白颐正的弟子,再加上他父亲李瑱也通晓诸子百科和诗文,所以他出身书香世家,饱读儒学经籍,信奉程朱性理学说。对于四书五经,他认为学习时应该先熟悉“四书”,再去学习“五经”。
高丽末年至朝鲜王朝初年,性理学者权近对于《易经》的研究和态度颇值得一说。权近认为,“五经”是一部各具独特特征,同时又相互关联的著作,而且各有其“体用”。这主要体现在他的《五经体用合一之图》和《五经各分体用图》两文中。他指出,《易经》包含全部“五经”的内容,所以相当于“全体”,而《春秋》则相当于“五经”的“大用”;因为他认为“五经”的作者是圣人,所以说“圣人即五经之全体,五经即圣人之大用”。“五经”的每本书都有其“体用”,《易经》的“体”(全体)是天地之理,“用”(大用)是圣人之道。他更进一步指出《易经》包含“五经”的“五经之体”,《易经》的大用是“道”,因为“五经”的“用”即《春秋》的“体”,是“道”。权近还有著作《五经浅见录》,其中《周易浅见录》分上、下经和《系辞传》《说卦传》四部分,没有《序卦传》和《杂卦传》。
值得说明的是,韩文的创制对于《易经》等儒家经籍在朝鲜王朝的传播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也是世宗对朝鲜文化作出的具有历史性影响的一大贡献。韩文 28 个字母在世宗二十五年(1443)创建完成,并于世宗二十八年(1446)予以颁布,世宗亲自将其命名为“训民正音”。普通老百姓如果没有学习汉字,就根本无法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创建韩文文字是为了解决自己国家没有文字而借用汉字的这一窘境。韩文创制后,世宗又指示用韩文来翻译《易经》等儒家经籍,这对解读儒学经典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儒学韩国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他们用韩文来对《易经》等儒家经籍进行“谚解”“口诀”,将其变为更为浅近的韩文翻译本,柳希春受王命而编写的《四书五经口诀谚解》就是一例 。此外,经筵讲《易》和殿堂论《易》的传统,也让《易经》在朝鲜半岛得到更好的传播。
韩国历史上,最知名的两位易学家分别是李退溪(即李滉)和丁茶山(即丁若镛)。李退溪被称为韩国的朱夫子。19 岁时,他曾一度痴迷《周易》,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周易》哲学思想。 c 受朱熹《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的启发,李退溪曾撰著《周易释义》《启蒙传疑》。从书名标题来看,这是对朱熹著作的回应和致敬,更是对朱熹易学思想的进一步探究,因“疑”而成就自己的易学思想和体系。李退溪 68 岁时(1568)所著《圣学十图》集中反映了他的整体学问思路。他首选《太极图》和《西铭图》来揭示天道的内容,将《太极图》作为《圣学十图》首章,与朱熹将《太极图说》作为《近思录》首章的意图是一样的,藉以说明圣学的根本目的首先应当是正确地理解作为 宇宙本质——太极的原理,然后才能正确地理解这种天道与人类的本质有着紧密的 伦理关系。在《太极图》中,他主要讲由无极、太极、阴阳、五行、男女、万物组成的宇宙的先天生成原理,提出“无极而太极”的宇宙生成论。在《西铭图》中以这种世界观为基础,论证了人在天、地、自然界的地位,从而明确了《易经》中天、地、人的“三才”之道。
丁茶山的易学研究自《易经》经传入手,他熟谙汉宋易学,可说是“旁求汉魏,以采九家之说,降及唐宋,博考诸贤之论” 。丁茶山的易学著作主要有《周易四笺》和《易学绪言》,其主要易学观点是义理与象数必须配合,反对只单独谈义理或象数。这种折中立场比较接近朱子。他治《易》兼采象数、义理,虽然严格上来说是以象数为主,但论象数时从不抽离文字。他亦强调“《易》词之文有象有占”,讨论文字不能置象数不理。林忠军指出,丁茶山推崇汉易,接受了虞翻的卦变说,但是并未照搬虞氏卦变说,而是发现了虞翻卦变说存在的问题,并对其提出较为深刻的批评;又通过检讨和整合朱熹、毛奇龄等人的卦变说,形成了融历法、筮法、易象为一体的独特卦变体系。丁茶山卦变说,以中国古代历法为依据,其内容显得更为合理;同时,他又修正了虞翻等人的卦变说缺陷,其逻辑更为清晰。因此,他丰富和发展了虞翻乃至中国古代整个易学史上的卦变说。
程颐的《程氏易传》和朱熹的《周易本义》于 14 世纪大约同时传入朝鲜半岛。《高丽史》中有两笔高丽博士到中国购买经籍的记录:一是金文鼎于元大德八年(1304)入元购买“六经”等书;二是柳衍于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入元购回经籍一万八千卷。又,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下科举诏,考试内容中的《周易》部分以程颐和朱熹的易学著作尤其是《程氏易传》和《周易本义》为主。尽管如此,朝鲜对于程颐《程氏易传》的接受要早于朱熹的《周易本义》,从禹倬开始,一直到李穑、郑梦周、郑道传等高丽王朝末年朝鲜王朝初年的学者都以程《传》为主要研究对象;直到权近的《周易浅见录》已开始略微重视《周易本义》,但还是以《程氏易传》为主;到一百多年后的李退溪的《周易释义》才完全偏重《周易本义》,并且明确宣称读《易》应以《周易本义》为先。尽管如此,朱熹的《周易本义》并未取得完全垄断的地位,偏好《程氏易传》的也不乏其人,大部分则是折中于这两者之间。
易学在韩国的影响更集中体现在韩国的日常生活中,例如,韩国安东市一直以来被誉为韩国精神文化的首都,韩国大儒李退溪即诞生于此。安东市在国际上最为知名的是两个文化遗产:陶山书院与河回村。陶山书院由李退溪所创建,河回村则是李退溪两大弟子柳氏兄弟宗宅所在。走进陶山书院和河回村,随处可见《易经》的痕迹,例如,书堂前出入处,掩以柴扉,取名“幽贞门”,得名于《周易》的《履》卦:“履道坦坦,幽人贞吉”;陶山书堂对面的院子外面有一眼古泉,题名“蒙泉”,可知直接得名于《周易》之《蒙》卦;再如,离安东不远的荣州有朝鲜最早的书院——绍修书院,书院中特有一个建筑叫作“直方斋”,这名字也正是来自《周易》之《坤》卦“直方大”;等等。可以说,韩国的儒家文化遗存大都留下了《周易》文化的印记,再加上韩国的国旗,这说明《易经》精神在韩国无处不在。
职是之故,在韩国参观之后,刘云超曾慨叹:“韩国的儒家文化和《周易》精神无疑来自中国,但是因为地域、习俗的不同,同一种文化以一种异国情调展现出来,会带给中国人以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当看到《周易》精神在韩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盛开如花影响深远,尤其是看到韩国社会对《周易》传统精神的历史继承与持守,足以让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汗颜不已。《周易》虽然源于中国,却属于全世界,它是中国先民为世界文化宝库贡献的一颗璀璨明珠。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和个人,如果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周易》精神,如果能更多地把《周易》精神融入自己的生命,就更有可能得到真正的幸福与和谐。”
韩国岭南大学教授、岭南大学文科学院院长郑炳硕教授曾指出,当今易学研究内容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远远超过古代,不仅涉及《易经》经传、《易经》哲学、中国古代易学家、韩国古代易学家、中韩易学比较研究、韩国易学史、易学断代史研究、出土文献研究,还涉及《易经》与管理学、精神分析学、符号学、政治哲学、书法美学、遗传信息等多元文化易学研究。
二、易学之“类”《易经》在日本
释义
《易经》具体何时传入日本,已不可考。一般认为,《易经》在公元 6 世纪前后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日本书纪》记载,公元 513 年从百济派来“五经”博士来日本,从此日本人开始学习《易经》和其他儒学经籍。日本著名文化史学者、儒学研究者王家骅认为,自 4 世纪末陆续东渡日本的“渡来人”或“归化人”,不仅把汉字传入日本,还把儒学思想传入日本。5 世纪,这些“归化人”及一些日本人写的文章中,已经部分体现出儒学思想的味道;日本人在 6 世纪开始系统学习“五经”等中国儒学经籍及其思想。美国著名清史专家、易学家司马富也指出,《易经》传入日本不迟于 6 世纪,但是直到 17 世纪才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德川幕府期间(1603—1868),日本刊刻了一千多部易学著作,比清朝时期中国所刊刻的易学著作还多,而清朝时期中国的人口是德川幕府时期的将近 45 倍。吴伟明则指出,尽管《易经》在日本古代(539—1186)未受重视,在中世纪(1186—1603)却受到重视,到德川幕府时期则臻至顶峰,成为当时日本最重要的中国经籍。也有学者指出,《周易》至少在9世纪中叶就已传入日本,经 12 世纪至 16 世纪日本中世时期的积累和发展,伴随着 17 世纪初朱子学的盛行,到了江户时代,开始形成日本学人传播、接受中国易学的兴盛局面。
《易经》在日本的兴盛,当然与这部书在中国得到足够的重视有关。但是,更重要的还是政治的实际需要。从德川时代伊始,《易经》便被用于弘扬德川儒学。德川初年,许多天皇和幕府将军在《易经》中寻求精神和实践指导。1680 年至 1709 年在位的幕府将军纲吉在 7 年时间里主持了至少 240 场《易经》研讨会,会上纲吉有时会亲自向听众讲授朱熹的《周易本义》,听众不仅包括他的亲信,还包括大名和其他高级侍从武士、地方官员、行政官员、佛教僧侣和神道禅师等。
《易经》之所以在日本兴盛,还有一个原因是《易经》常被用于支持“臣忠于君”这一儒家核心概念。根据就是《易经·序卦》所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 藤原惺窝的高徒、朱子学派儒者松永尺五就持这种观点。同时,《易经》也支持幕府将军独特的统治地位。正如六爻的爻位中,二、五爻为最重要。也许有人认为君主要居上位,不过这样有违天道,正如《易经·乾卦》有言:“上九:亢龙有悔。” 17 世纪的日本学者朝山意林庵(也称朝山素心)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易经》对日本的影响非常深远,渗透到日本人日常生活和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
《易经》研究在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被制度化。例如,日本教育部门将其视为儒家文本,占卜部门则将其视为占筮之书,等等。所有这些都是通过注释《周易》本经和《易传》以阐明义理,属义理学派。尽管如此,《易经》在古代日本却并不受重视,当时更受重视的是《论语》。藤原佐世曾辑录《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该书于宽平年间(889—898)辑成,是日本现存最早的汉籍目录,《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易家》著录了33 种共 177 卷与《易经》有关的中国经籍。这从侧面说明,在日本古代时期,人们对《易经》的关注度并不高。
到了日本中世镰仓幕府时期,《易经》开始在日本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对《易经》的重视引起了日本对《易经》的重视。随着隋唐时代遣隋使、遣唐使的大批来华和归国,他们将中国士绅阶层对于《易经》等“五经”的研究及其态度也带回了日本。尤其是 13 世纪前后,《易经》与新儒学的兴起而形成的互动关系更是让日本学界对《易经》发生很大的兴趣。由于《易经》为新儒学构建了形而上的架构,程朱学派对于《易经》也越来越重视,这就更加保证了新儒家在中国的兴起。中国学界的这种互动反应,也直接通过遣唐使等传到了日本国内,进而影响了日本学界对《易经》的态度。同时,日本僧侣的作用也不可小觑。在中世日本,僧侣在知识生产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五山禅林的僧侣成为《易经》研读的主要力量,他们对《易经》的研究、点校和注疏以及对中国《易经》注疏的翻刻,都直接影响了《易经》在中世日本的流通和传播。同时,中世日本也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易经》的“易”思想契合了日本的时代思潮,从而营造了较为顺畅的接受环境。最后,《易经》与日本本土信仰也有契合之处。例如,日本的神道教就吸收了《易经》的阴阳思想和中国的五行思想。有学者就指出,江户时代日本学者推进易学本土化,使之和日本传统的神道文化沟通、融合,形成以“和魂汉才”或“和魂汉魂”混融为特色的“江户易学”。
伊藤仁斋是日本江户时代的著名易学家,是古义学派代表。他的易学著作主要有《语孟字义》《易经古义》《周易乾坤古义》《大象解》和《童子问》等,他还曾将程颐《伊川易传》与朱熹《周易本义》合刻为一而得《周易经传》,其易学思想由此可见一斑。他长期致力于探索和诠释中华易学的内涵义理,发展出了他自己的见解,成就卓著,形成了日本易学史上可称“仁斋易学”的义理学体系。他的儿子伊藤东涯也是著名的古义学易学家,《周易经翼通解》是他最著名的易学著作。
很有意思的是,日本的易学学派之间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朱熹的“易本卜筮之书”这一观点上,有些学派支持,有些学派反对,有些学派则似乎居中,既不支持也不反对,或者说既支持又反对。例如,古义派的伊藤仁斋就对朱熹的这一观点极力批评,他说:“倘以易为卜筮之书,则易林元龟之属耳。岂是与诗书春秋同列于六经哉?从义则不欲用卜筮,用卜筮则不得不舍义……若以易为卜筮之书,则是易为小人谋,而非为君子谋也……浩浩《易经》,才为一事之用,而不足以为人伦日用应事接物之法,家国天下经世垂范之典,岂足尚乎!” 董灏智指出,朱熹等理学家在吸收佛教、道教思想的基础上为先秦儒学填补了形而上的理论体系,而这些内容又被朱熹添加到易学诠释之中,尤其是其中的“太极”“理气”“未发已发”“格物穷理”“心统性情”等说法。而与此相反,仁斋对“易”的认识,更侧重于形而下层面的人伦日用之道的发挥,这正与他的古学取向相得益彰,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古义学易学”。同为古义学派的荻生徂徕却因此批评伊藤仁斋道:“夫卜筮者,传鬼神之言也。无鬼神则无卜筮,有鬼神则有卜筮。既以尊鬼神为非孔子之意,则废卜筮亦其所也。”与之类似,徂徕的学生太宰春台也是从卜筮的社会功能的角度来批评伊藤仁斋。
与太宰春台不同,森东郭则说:“卜筮者《易》之用也,使民由之之道也。故孔子曰‘不占而已’。试问彼所谓卜筮,果何事乎?纳甲飞伏之妄说,以欲神德行乎?固哉。”于此,陈威缙指出,相较于春台将卜筮视为易道的全盘本质,东郭在此显然更重视一种超越于卜筮具体作用之上的“道”。
日本朱子学的杰出代表山崎闇斋却重视卜筮,编著了《朱易衍义》,认为“学者苟能读此,则知易本卜筮之书,四圣之易各别,而程子之易又别也”,力图恢复朱熹的易学观。当时重视卜筮而批判伊藤仁斋的尚有仁斋的学生佐藤直方、闇斋的高足浅见斋,以及折中学派的儒者寺门静轩,等等。
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伊藤仁斋的很多著述都未完成,都是由其子伊藤东涯来完成的,例如,他的重要著作《易经古义》和《大象解》。可以说,东涯所著多种易作中对于易学基本知识的入门详解,对于易学流派的辨析梳理以及与象数有关的卦变、正策余策诸说等,无一不是对仁斋易学的发展、推进与完善。因此,仁斋的易学由其子东涯发扬光大,在为古易学增添魅力的同时,也推动了江户易学的发展。
总之,仅伊藤仁斋一人的易学研究就引起了诸多反应,中世、近世日本学的繁荣由此可见一斑。日本易学的主要流派有朱子学派、阳明学派、古学派。但是阳明学派事实上影响并不大,在社会上几乎没有形成持续的思想影响。或者可以说,日本的阳明学只是作为一种思想倾向而存在。而前文提及的伊藤仁斋和荻生徂徕等,都是古学派的代表人物。
日本《古事记》序文认为,天地生于“混元”,“混元”之上没有如《道德经》所说的主宰者——“道”(无)。而以《易传》为代表的儒家系统的宇宙生成论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周易·系辞传》),就是说天地生于“太极”。所谓“太极”,根据孔颖达的《周易正义》的解释“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也”,“太极”为混沌之元气,是“有”,是作为天地依据的本源性物质。也就是说,与道家系统的宇宙生成论相比,日本的宇宙生成论更接近以《易传》为代表的儒家系统。
以《易经》为代表的儒学传入日本后,与日本各种信仰处于共存状态,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政治原因,当时律令国家的统治阶级希望借助所有宗教、思想的力量来确立他们的权威;二是文化原因,当时日本人惊叹于远比自己固有文明卓越的中国文明(包括儒学和佛教等),对渐次传来的新事物、新经籍的崇敬之情非常强烈,行之并笃信之就自然而然了。
以宫廷和贵族势力为背景、汉唐训诂为主要内容的日本早期儒学,在镰仓时代已经没落。不过,在镰仓、室町时代的精神生活中,居支配地位的依然是佛教而不是儒学。这也是日本古代,以《易经》为代表的儒学未能成为日本社会主流理论的主要原因。
藤原惺窝脱离禅门,还俗转向儒学,是日本儒学独立的标志。藤原惺窝“脱佛转儒”既受到中国的思想影响,也受到朝鲜朱子学的影响。《四书五经倭训》的编纂,标志着藤原惺窝向儒学的转变。不过,藤原惺窝并非纯粹的朱子学学者。日本朱子学派的真正开创者是藤原惺窝的弟子林罗山。日本的朱子学者(除室鸠巢之外)中,无论是林罗山,还是山崎闇斋、贝原益轩,大都信奉神儒一致,以朱子学的思维方法阐释神道,倡导神儒合一说,也带有一定的神秘主义色彩,这一点与中国、朝鲜的朱子学不同。
江户时代后期,以《易经》为代表的中国儒学在日本逐渐衰落,即便是批判徂徕学派的折中学派也未能挽救其颓势。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日本人的西洋文明观的转变。这种转变主要依托两大事件:一是洋学(兰学)的输入;二是鸦片战争中国战败。随着兰学的传播,日本人的西洋文明观开始发生变化。此前,由于深受儒学中“华夷”思想影响,日本人认为西洋诸国在伦理、文化上都处于劣势。但是,随着兰学的输入,他们开始承认西洋诸国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尤其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败北给了日本人极大冲击。以此为契机,日本人不仅不得不承认西洋科学技术的优越性,而且开始主张吸收西洋科学技术。同时,也有一些儒家学者想通过重新解释儒学的概念和理念,试图调和儒学和西洋文明。例如,佐久间象山和横井小楠就是其中的代表。尽管如此,他们的思想还未能脱离儒学的框架,从其思想中也能听到日本儒学衰落和近代思想前进的足音。
从此之后,以《易经》为代表的儒学在日本的地位再也无法恢复到江户时代。但是,明治维新时期,儒学有所恢复,尤其是在西村茂树的《日本道德论》中,儒学经过改变而得以重生。1890 年日本政府颁布的《教育敕语》确立了以儒学道德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方针及国民道德方针,不仅影响了日本的近代教育,而且还广泛而持久地制约着日本近代的思想。明治维新之后,儒学自然观的影响基本消失,而儒学道德观却与日本的国家主义意识相结合而继续存在。这也直接导致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膨胀,其中以儒家德目为基本内容的“武士道”精神遭到恶用。更为恶劣的是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一种日本型的法西斯主义,也与儒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儒家道德则被恶用为高扬战意的手段,从而成为侵略中国乃至亚洲各国的宣传工具。
“二战”后,《易经》在日本的地位又渐渐恢复,各种各样的译本和研究性著作不断出现。例如,今井宇三郎持续地对《易经》进行译解和研究,1958 年今井宇三郎著有《宋代易学の研究》,由明治图书出版社出版;1987 年,今井宇三郎著《易经·上》(新译汉文大系的第 23 种),1993 年著《易经·中》(新译汉文大系的第 24 种),2008年他与堀池信夫、间嶋润一合著《易经·下》(新译汉文大系的第 63 种),都由明治书院出版。
再如,1969 年,高田真治和后藤基巳翻译的《易经》(岩波文库)上、下两册,由日本知名出版社岩波书店出版,该译本 1993 年由同一出版社再版;1976 年诸桥辙次著的《中国古典名言集 3——诗经·书经·易经》(讲谈社学术文库· 中国古典名言集)由讲谈社出版;1994 年桜左近著的《易经新译》由近代文芸社出版;1995 年,田中恵祥著《易经入门——自分で占える易の実践》,由ダイヤモンド社出版;1997 年公田连著《易经讲话(全 5 卷)》由明德出版社出版;1998 年,由医道の日本社出版《まんが易経入門——中国医学の源がわかる》;1999 年,小林三刚著《易经と乾为天——水雷屯の实践解说》,由绿书房出版;2003 年,金谷治著《易の話——〈易经〉と中国人の思考》(讲谈社学术文库),由讲谈社出版;2005 年,竹村亚希子著《リーダーの易 易经——时の变化の道理を学ぶ》,在 PHP エディターズ·グループ出版;2015 年 92岁的梶川敦子著《のひとりごと——〈圣书〉と〈易经〉に生きて》,由青弓社出版;2015 年,冈本吏郎在朝日新闻出版社出版《ビジネスパーソンのための易经入门》;2015 年,远山尚在明德出版社出版《煌く易经——未来に生きる东洋の神秘的精神》,等等。这只是笔者目力所及看到的极少一部分,但是可以看出《易经》在日本依然是热门话题。
三、《易经》在越南及其他亚洲国家
以《易经》等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对越南的影响,11 世纪中叶是一个分界点。刘正指出,越南在汉朝末年或许就已经有了易学研究,《易经》等经籍的传入则更早,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特别是作为一个儒家文化圈所属国,其易学研究则开始于 1070年以后,在此之前的越南易学研究史,只是中国易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陈益源指出,越南自后黎朝、阮朝独尊儒术并建立完善的科举制度之后,中国儒家经典不断传入越南,从 17 世纪到 20 世纪,儒家的四书五经全部都被翻译成越南喃字,更加巩固了儒家思想作为越南国家正统思想的地位。
明朝统治越南期间,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广揽人才、重用儒生;二是永乐十七年(1419),派监生唐义向越南颁赐《性理大全》;三是在各府州县“设立文庙”,开设学校,使得程朱理学广为传播,孔子和儒学的影响进一步深入各地州县。
黎圣宗光顺八年(1467),在越南首置“五经”博士,并颁官版“五经”于国子监:“光顺八年三月,初置五经博士,时监生治《诗》《书》经者多,习《礼记》《春秋》《周易》者少,故置五经博士,专治一经,以授诸生……夏四月,颁五经官板于国子监,从秘书监学士武士祯之言也。”
与朝鲜半岛和日本一样,朱熹也是越南儒学中非常重要的资源,大部分学者都受到他的影响,只是程度深浅不一。随着儒学和科举制度向越南传播,朱熹的影响在黎朝和阮朝前期达到顶峰。越南最重要的易学家,前有黎贵惇,后有黎文敔。
黎贵惇无疑深受朱熹和程颐的影响。正因为受到朱熹理气思想的影响,所以他将“理气”置于《芸台类语》的首篇。《易肤丛说》疑为黎贵惇所作,主要采用答问的方式,论述了作者对程、朱《易经》传义的理解和见解。黎文敔是越南阮朝最为著名的易学家,著有《周易究原》《论语节要》《大学晰义》《中庸说约》《礼经主仁》等,其儒学见解主要在于强调“伦常之道”(人道)和“阴阳之道”(天道)的关系,认为儒学是“以人合天”的学问,而《周易》之道是儒学的根源之道。由此可见,《易经》在黎文敔的学术生涯中的重要地位。
《易经》在越南的影响不如在朝鲜半岛和日本大,有其自身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文字。越南曾经长期使用汉字;于 6 世纪前后盛行的喃字,是越南主要民族京族使用的文字,而且还用来翻译过《易经》等儒学经籍;法国殖民越南后,又采用拼音文字,使用拉丁字母书写。可以说,这三种文字是不相通的,需要通过翻译才能达到相互理解和沟通。这样一来,现代越南人如果要理解古代传下来的以《易经》为代表的中国经籍,必须通过翻译才能看懂。
新加坡等其他亚洲国家,因为其居民中有很大部分是华人,他们与国内亲属,或通过生意往来结交的人,都同属于一个文化圈,都深受以《易经》为代表的儒学的浸润,所以他们都或多或少了解一些易学思想和儒家价值观。尤其是东南亚地区,不仅成为华人华侨的一个高集中居住区,而且从历史上看,也是华人华侨与祖国联系最为密切、历史最为悠久的地区。更为重要的是,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在保持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秉持着一贯的积极作风,因此此处堪称当今世界上对以《易经》为代表的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保留得最好最完整的地区之一。
新加坡是华人占多数的国家,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文化自然也就成了新加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移居新加坡的华人大都是底层民众,尽管受教育程度不高,甚或目不识丁,但由于自幼生长在儒家社会环境中,耳濡目染,也深受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熏陶和影响,即便远离祖国,也仍然保持着儒家行为规范,将儒家文化传统一并带到了新加坡。对此,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也深有同感,认为新加坡华人华侨在日常生活里施行儒家的道德教义,他们所具有的道德品质都是从父母和家人那里学来的文化或民间风俗。正是靠着这种生活化的、日积月累的作用,儒家文化才得以在新加坡扎根并持续传播,并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和 20 世纪 80 年代先后出现的两次儒学复兴运动奠定了群众基础。这两次儒学复兴运动,与新加坡政府的积极推动也有直接的关系。一是 1877 年在新加坡先后成立了两个专门管辖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官方组织:第一,殖民地政府设立了所谓的华民护卫司;第二,清朝政府设立了它的第一个驻外领事馆——新加坡领事馆。这是儒家文化在新加坡传承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直接导致了 1899 年至 1911 年间在东南亚以新加坡、马来西亚为核心而爆发的范围广阔、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孔教复兴运动。这一次儒学复兴运动,还使得华人学校得以创立,儒家思想通过华校里的华文教科书,以潜移默化的方式,继续影响着华侨的思想意识。二是 20 世纪 80 年代的“儒家伦理”教育运动。需要说明的是,新加坡的第二次儒学复兴与李光耀对其的关注密切相关。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也有很多华人华侨,但是由于其政府没有像新加坡政府这样直接介入儒学的传播,而是靠华人华侨之间自发、自觉地传播,所以这些国家儒学传播的势头没有新加坡那么强劲,而更多像一股潜流,在社会思想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东亚、东南亚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华人华侨对《易经》所代表的儒家传统文化的传播发展,其作用不可小觑。“源源不断、持续不断的中国移民,就是儒家思想文化的实际携带者和传播者。” 就这样,《易经》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亚洲各国旅行,对这些国家产生着或大或小的影响。
四、东亚易学与国际易学
在讨论亚洲易学的过程中,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东亚易学对国际易学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东亚易学与国际易学发生关系,有着多重原因。其中最为主要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结为如下几点:一是易学本身吸引国际学者关注;二是有些学者通过英语进行易学研究,从而引起国际学者的注意,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位学者是吴伟明(Benjamin Wai-ming Ng)教授,其次司马富教授和范多思(Paul G.Fendos,Jr.)博士也为易学在西方的传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吴伟明于 1990 年到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其导师是日本德川明治时代的一代宗师马厄利尔·詹逊(Marius B.Jansen),1996 年以博士论文《蜀葵与六十四卦:德川幕府思想文化中的〈易经〉》( The hollyhock and the hexagrams: the I Ching in Tokugawa thought and culture)获得博士学位。吴伟明又用了近 5 年时间继续完善这一书稿,终于在 2000 年由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及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共同出版,书名改定为《〈易经〉与德川思想文化》( The I Ching in Tokugawa Thought and Culture)。该书出版后,反响很大,出现了多篇书评,比如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历史系 Gregory Smits 教授在著名汉学研究刊物《亚洲研究期刊》(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上指出,《〈易经〉与德川思想文化》是一部基于扎实学术研究的原创作品,研究德川文化的学生应该更仔细地研究《易经》的作用;荷兰莱顿大学的 W. J. Boot 指出,吴伟明认为《易经》是德川幕府日本最受欢迎的中国经典,在知识和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无处不在;曾著有《儒学与德川文化》( Confucianism and Tokugawa Culture,1997)一书的美国南加州大学 Peter Nosco 教授曾在著名的《哈佛亚洲研究学报》(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上评论道,吴伟明的研究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学术研究,为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知识和文化史做出了重要贡献;牛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退休日语讲师、荣休研究员,专攻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历史文化(特别是儒学史)的詹姆斯·麦克马伦(James McMullen)在《日本学志》( Monumenta Nipponica)上评论道,毫无疑问,吴伟明成功地证明了日本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如何不可分割地归功于中国,这种债务从儒家思想的伟大传统延伸到解决日常生活难题的实用占卜的小传统,因此这本书在北美著名汉学家傅佛果(Joshua A.Fogel)教授主编的这个新系列(即Asian interactions and comparison)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这部书在 2001 年 1 月获得了全美图书馆协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的“2000 年度优秀学术著作”奖(2000 Choice Outstanding Academic Book);同年 2 月被全美大学出版社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y Presses) 列 入“1999 至 2000 年 度 重 要 大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专 书 ”(Significant University Press Title, 1999—2000);同年 6 月获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提名角逐日本及韩国研究最高荣誉的“约翰·河路学术书籍奖”(John Hall Book Prize)。在著名易学家郑吉雄教授的建议下,吴伟明将其专著进行翻译和扩充,最终在 2009 年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易学对德川日本的影响》一书。
正是由于有了吴伟明、司马富和范多思等熟谙英语并积极用英语进行著述的易学家的努力,易学研究经过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而传播到了欧美诸国,对这些国家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从而使《易经》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进而形成了国际易学研究的雏形。
文章来源
《洙泗学报》第一辑
编 辑 | 陈心茹
以生命点燃生命 以智慧点燃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