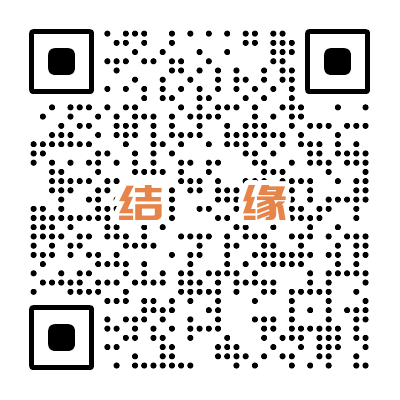刘彬|孔子哲学思想三论
作者简介

刘彬(1965—),男,字於易,山东滕州人,曲阜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东亚易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孔子文化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周易学会常务理事,山东周易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出土易学文献、《周易》经传、象数易学、儒家哲学,建立《易经》古义研究新体系,正在致力于易图学的挖掘、重构以及易图学派的创立。 主要内容 摘要 孔子的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人文的定位,生命价值意义的开显,以及道德生命的达成三个方面。在人神关系上,孔子“敬鬼神而远之”,以中和的智慧,将信仰和理性圆融地和谐为一体,将宗教内在地人文化。在对个人生命的安立上,孔子通过对“命”的反省,对“义”“利”的分辨,为人类开显出一个道德世界,挺立起人的道德生命,从而解决人的安身立命的终极关怀问题。在道德生命的达成方面,孔子建立起“仁道”思想,也即道德践履的学说,这一学说要求成就道德人格,实现道德的世界。总的来看,讲求理性和情感的交融和谐,追求道德化和人文化,是孔子哲学的基本特征。 关键词
孔子;哲学思想;人文化;道德世界;道德践履
所谓孔子的哲学思想,是指孔子提出的关于人如何安身立命的一些观念,以及终极解决人之存在问题的一些操作方案。这些哲学思想,是孔子紧紧扣住人之生命存在的终极意义问题,而所作的理性反省和心灵了悟,是人类东方智慧的一次灵光乍现。这些哲学思想,超越于世俗生命和生活,同时又发于和入于世俗生命和生活,并实现于世俗生命和生活。一言以蔽之,孔子的哲学,是即生活而超生活,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二千多年来,孔子的哲学思想,对中华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和人格的塑造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对东方文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哲学思想,在人的生命枯萎,人文关怀淡漠,价值意义缺失的现代社会,更显现出重大的价值。因此,对孔子的哲学智慧,我们必须以当下的生命实感,去同情地了解和真切地体会,从而将其化入我们的生命,化除生命存在的焦虑,达成我们存在的意义。笔者认为,孔子的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人文的定位,生命价值意义的开显,以及道德生命的达成等三个方面。下面我们作一具体分析。 一、敬鬼神而远之——人文的定位 孔子的哲学思考,是从人在世界中的定位开始的。而人的定位,是孔子在处理神——人关系中获得解决的。 神与人的关系,或鬼神与人的关系,是古人要面对和处理的最重要的关系之一。鬼神信仰,即“神道”,本为夏商周三代的宗教传统,孔子继承此传统,敬重鬼神,重视祭祀。据《论语》记载:“子之所慎:斋,战,疾。”“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论语注疏》,第26页)“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注疏》,第35页)孔子对关于鬼神的祭祀很慎重,认为不是自己应该祭祀的鬼神,却去祭祀他,这是献媚。在祭祀时,如果自己不能亲自参加,决不请别人代理。孔子对人格神的“天”很敬畏,认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注疏》,第36页),认为君子有三畏,第一畏即“畏天命”(《论语注疏》,第228页) 但孔子与传统宗教信仰又有不同,他反对对鬼神狂热的、迷乱的、非理性的盲信,认为对鬼神应保持信仰,但同时又要保持理性。据《论语·述而》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注疏》,第92页),对于爱好怪异、乱智迷信、过分媚神等行为,孔子是批评鄙弃的。《论语·雍也》篇记载,学生樊迟问孔子“知”,孔子回答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也。”(《论语注疏》,第79页)恭敬信仰鬼神,但不过分亲近,而是保持理性,疏远他,与其保持一定距离,孔子认为这才是明智的态度。信仰和理性,一般来讲,二者为互相矛盾不相容的两物,但孔子把二者圆融到一起,表现很高的“中和”智慧。这种“中和”的圆融,从孔子对鬼神“如在”的态度,可看得更清楚。《论语·八佾》说:孔子“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注疏》,第35页)孔子祭祀鬼神时,神色庄严,态度恭敬,就好象鬼神真的降临、真的存在一样。鬼神,本为玄远幽微之事,是否事实上存在,本来是理性所不能解决的“二律背反”。因此,如果完全付诸于理性,完全以主客分离、证实或证伪的知性态度对待宗教,就会执定宗教荒唐而完全否弃之。实际上,鬼神宗教乃是信仰,人信其“有”,此“有”不是事实上的、存有论的“实有”,乃是人情感需要的“应有”,是“信有”,是“情有”,从实质上说,乃是一种价值论之“有”。如果执定鬼神之“应有”为“实有”,就会完全匍匐于鬼神之下而成为迷信。因此,必须以一种价值理性,更准确地说是一种价值智慧,来提醒、警惕此信仰,使此信仰不被放纵而成为迷信。因此,孔子对待鬼神,将“在”与“不在”统一起来的“如在”态度,既不将信仰与理性相互吞没,又不将二者相互隔离,而是以中和的智慧,将二者圆融到一体。 将信仰和理性统一,以理性来“过滤”“纯化”信仰,在人神的关系中远神而近人,保持与神交通的宗教情怀,同时更注重人事,可以说,孔子将“神道”做了一番“洁净精微”的工作,将宗教大大地人文化了。孔子的“事人”“事鬼”之辨、“知生”“知死”之辨,鲜明地说明了这一点。据《论语·先进》载,子路问服事鬼神之事,孔子回答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注疏》,第146页)子路又问死之事,孔子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注疏》,第146页)从孔子的直接答语上看,他是说,不能事人,就不能事鬼;不知生的道理,就不知死的道理。而从内在深层上看,孔子要表达的是这样一种观点:事人就是事鬼,知生就是知死;在“事人”的“人事”中就完成了、了结了“事鬼”的“鬼事”,在“生”中就完成了、了结了“死”。这是把“鬼事”寓于“人事”,把“死”寓于“生”;或曰把“鬼事”托付于“人事”,把“死”托付于“生”。这是一种高超的人鬼、生死转化艺术:把“鬼事”转化为“人事”,把“死”转化为“生”。由此,人在此生命中,尽此人事,就同时完成了鬼神之事;不是在人事之外,还有鬼神之事。因此,不是外在地弃绝鬼神,否弃宗教,而是进行内在的转化,把宗教转化为人文,把神性寓于人事,这就是孔子处理人神关系的基本精神。 孔子的易学思想就表现了这种精神。据《论语·述而》记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注疏》,第91页)《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曰:‘假我数年,若是,我於《易》则彬彬矣。’”《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太史公曰:盖孔子晚而喜《易》。”(《史记》,第1903页)《汉书·儒林传》曰:“(孔子)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可见孔子晚年研《易》好《易》。但很多学者不相信传世文献的这些记载,认为孔子和《易》没有关系,孔子没有自己的易学思想。新出土文献证明传世文献的记载是真实的,孔子确实形成了自己的易学思想。1973年出土的马王堆帛书《易传》,其中的《要》篇载:“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子赣(贡)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諏)之,赐缗(惛)□(卜筮之类的词)之为也。夫子何以老之好之乎?’夫子曰:‘……予非安亓用也。’[子赣(贡)曰:]‘夫子今不安亓用而乐亓辞,则是用倚(奇)于人也,而可乎?’……子赣曰:‘夫子亦信亓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亓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亓祝卜矣!我观亓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可补为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亓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亓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世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亓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亓后乎?’”卜筮乃人与鬼神交通之事,孔子对卜筮之《易》有两点基本看法,也是他新易学观的基本观念:其一,孔子也信其卜筮,也进行过筮占,即对鬼神存有信仰,这点与祝巫卜史的态度一样,即“同途”。其二,但孔子与史巫又有很大不同,史巫是通过幽赞、明数,而将人的吉凶祸福完全托付于鬼神,而孔子则是对鬼神远之,要求人们祭祀而寡、卜筮而希,应观人自己的德义,以自己的德行求福,以自己的仁义求吉,这是要求把人的吉凶祸福寄托于人自己德义的人文世界,这是孔子为人类指出的一条新的路向,这是与史巫的“殊归”。 孔子将宗教人文化,将神事转化为人事,实际上是要解决人在世界中的定位问题。在古人的观念中,世界是天地人鬼神合一的存在。在人和鬼神的关系中,鬼神为主宰,人为附庸。对这种存在论意义上的观念,孔子并不否认,但他认为,人的存在定位,既不能放在神位上,也不能放在鬼位上,而只能放在人位上。鬼、神和人各有其职分,应各守其分,各尽其职。人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人自己的存在中,就在人自己的这个位置上。人不能把自己托付于鬼神,不能把人事托付于鬼神之事。总之,人在宇宙中有自己的位置,人的存在必须定位在人位上。 二、人之生命的安立——道德世界的开显 孔子在人神关系上,将神性寓于人事,将宗教人文化,表示孔子实际上关注的是人的问题。对人的生命存在的深层焦虑,对人如何安身立命的终极关切,是孔子作为哲人的终生情怀。也正是在这里,孔子为人类开显出一个道德世界,在人的气物生命外挺立出道德生命、价值生命,在物的世界中创造出价值的、人文的世界;而儒家之成为儒家,儒学之成为儒学,孔子之成为儒家、儒学的开山,也正表现在这里。 这一道德世界是孔子在对“命”的反省,对“义”和“利”的分辨中开启的。据《论语·颜渊》记载:“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注疏》,第159页)《论衡》的《命禄》篇、《问孔》篇、《辨祟》篇皆引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曰:“(子夏)盖闻之夫子。”可见“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应是子夏闻之于孔子、孔子所说过的话。生死寿夭富贵贫贱,乃是人的生命存在的物的、气的层面,或曰是人的生物生命、气质生命,而这种生命的存在形态决定于人之外的力量,是受人之外力量的限定。孔子称这种对人生物生命、气质生命决定、限定的力量为“命”或“天”,“死生有命”的“命”乃外在命定,“富贵在天”之“天”乃外在主宰,此“天”“命”不论是无意志的外在力量,还是有意志的人格神,“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都表明人的存在的“外在性”:人的存在完全决定于外在,此外在是人不能参予的,是人无能为力而只能听从的。在人生物生命、气质生命的外在决定下,对人来讲,人的存在是偶然的,人的存在是无根的,人的生命是得不到安立的。在这里,生命只表现出无意义性、无价值性。 人的这种无意义、无价值的存在世界,孔子称之为“利”的世界。所谓“利”,乃指功利、功用而言。《论语·里仁》篇记孔子话说:“小人喻于利。”(《论语注疏》,第51页)一般人(“小人”)不待教、不用习,就能精明地知晓他生存世界的功用性。在他们(“小人”)的眼里,这个世界只是个“利”的世界,一切事物(包括人)的存在只表现出他的功用性、工具性、手段性,一切事物(包括人)只能作为功用、工具、手段而获得存在。因此,在这种“利”的世界里,人的存在只能表现出无目的性。反言之,在“利”的世界里,如果说人的存在有“目的”的话,只能是为存在而存在,也即为生存而生存,显然这时人已同于一“物”,那里还有“人”存在的意义呢? 因此,不管是“天命”所决定的人的存在的外在性,还是“利”的世界的功利性,都表现出人生的无根,无价值,无目的,无意义,都不能使人安身立命。对于人的这一存在焦虑,孔子由“利”达“义”,严分“义”“利”,开显出一个“义”的世界,从而使人的生命真正得以安立,为人确立起价值之源。《论语·里仁》篇记:“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注疏》,第51页)朱熹注曰:“义者,天理之所宜。”(《四书章句集注》,第73页)所谓“义”,即“宜”,指应该,应然,即人之所当然者。孔子指出,与一般人(“小人”)只知晓“利”的功用性不同,君子明了“义”之应该、应当。孔子说:“君子之於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四书章句集注》,第71页)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判断其可与不可,其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是否符合“义”,是应当还是不应当,故“君子义以为上”(《论语注疏》,第244页)“君子义以为质”(《论语注疏》,第213页),君子崇尚“义”,以“义”为本。 孔子“义”“利”对举,严分“义”“利”,实际上是划分开人之存在的两个世界:应然世界和必然世界。必然世界即事实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一切存在都受因果律的铁的决定,都跳不出无情必然的桎梏。对人来说,人作为“物”的、“气”的存在就处于必然世界中,这时人的存在就完全锁定于因果链条中,人的生命存在即命运就完全地被外在必然决定。在这个世界中,人只是作为一“物”,为实现外在必然而挣扎,为存在而存在,人只是作为功用性而存在,换言之,在这个“利”的事实世界中,对人来说,人自身的存在是无价值的,人只是外在必然性的工具。因此,“利”的事实世界是无价值的世界。而“义”的世界则是应然世界、当然世界,是人的价值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之所为乃基于人之当为,人完全承担并自觉履行人之当为,人自身作为目的而存在,人以价值方式存在。因此,在“义”的价值世界中,人实现了自己的生命价值,或曰人获得了价值生命,人的生命得到了真正的安立。 “义”的价值世界即“道德”的世界。人之所为的价值具有超越性的“天道”意义。《论语·公冶长》载:“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注疏》,第61页)子贡不闻之言,正反证孔子曾言“天道”,只是子贡不闻而已。“天道”为超越的价值之源,孔子以形上智慧,于此有深深的契会。《论语·泰伯》记:“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注疏》,第106页)这里的“天”应指超越的义理之天,尧能契会此超越的“天”并效法之,因此得到孔子深深的赞许。《论语·里仁》记:“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注疏》,第50页)只要闻到“道”,马上去死都可以,可见孔子对“道”的追求,其情何切!此“道”绝非寻常小道小理,亦绝非普通小智小慧所能了悟。此“道”至大,义理深微,朱子对此的抉发颇中其奥,其曰:“道者,事物当然之理。苟得闻之,则生顺死安,无复遗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时之近。”(《四书章句集注》,第71页)因此,其“道”乃指超越的、当然的价值之源,是一种形上究竟存在。追求此“道”,乃是人生的第一要务,对此孔子屡屡谆谆言之:“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注疏》,第216页)“守死善道”(《论语注疏》,第104页)“志于道”(《论语注疏》,第85页)“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注疏》,第48页)“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注疏》,第50页)。 此超越形上的“道”落实于人即为“德”。只讲“道”,有虚悬落空的危险,故必须讲到“德”,才能将“道”在人身上落实下来,故“道”“德”必须并言。《论语·述而》记:“子曰:志于道,据于德。”(《论语注疏》,第85页)朱子注:“志者,心之所之之谓。道,则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是也。据者,执守之意。德,则行道而有得于心者也。”(《四书章句集注》,第94页)故“德”即“得”,即在人心上得于当然之“道”。而当然为“义”,道德的内容即为“义”。子张问孔子何为“崇德”,孔子回答说:“主忠信,徙义,崇德也。”(《论语注疏》,第162-163页)樊迟亦问孔子何为“崇德”,孔子很高兴,回答说:“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乎?”(《论语注疏》,第167页)“崇德”的主要内容是“徙义”,即“见义则徙意以从之”(包咸《论语包氏章句》),即了悟并执定其“义”之当为而为之。“崇德”又为“先事后得”,“事”即为,即“为所当为,而不计其功”(《四书章句集注》,第139页),所为的也正是“义”。因此,“道德”的行为即“义”的行为,“道德”世界即“义”的当然世界、价值世界。此“道德”世界又是由人之所为而形成,离开人,也无此世界,因此,此“道德”世界又是“人文”的世界,即人文世界。 总之,孔子急于人之存在焦虑,通过对“命”的反省、“义”“利”的分辨、形上价值之源“道”的契会、“德”之人为的落实,在人的“物”的生命、“气”的生命之外,为人类开启出价值世界、道德世界、人文世界,使人的道德生命挺立而出,从而真正解决了人类的安身立命这“第一问题”。 三、过仁者的生活——道德生命的践履 使人安身立命的价值世界、道德世界,其价值之源本之于“天道”,具有超越的形上性,但它不是人只能仰望而不能达至、只能思慕而遥不可及的“天国”,实际上恰恰相反,人之实践性正是价值世界、道德世界的最基本特征,离开人之行为,价值世界、道德世界是不存在的。因为价值世界、道德世界同时是人文世界,是人之当为所形成的世界。因此,道德世界的实现,道德生命的获得,就是人的道德践履的问题。 孔子为人类所开辟的实现道德世界的方法,就是“仁”的道路,也即“仁道”。“仁”的世界即道德的世界,“仁”又关乎人,它又是人的道德生命。行仁道即作道德实践,从而使我们的道德生命得以挺立,得以生长。具体言之,仁道有下述内涵: 其一,行仁的目的是成就个人的道德人格,仁道为己。《论语·宪问》记:“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注疏》,第195页)《论语·卫灵公》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注疏》,第214页)道德修养(即《论语》所谓“学”)是为了成就、完成一种个人人格,这种个人人格,孔子称为“君子”,或称为“仁者”,也就是说,“仁者”或“君子”表示的是一种人生境界,是一种人所追求的、能够实现人的道德价值的人格形态。因此,仁道即个人成德之道,仁学即个人成德之学,行仁就是为了成为“君子”,成为“仁者”,行仁即可当下从自己做起,在自己的身心上笃实地做工夫,“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从而“归仁”(《论语注疏》,第157页),故“君子求诸己”。而“为人之学”是名利之学,是功利之学,是“利”的事实世界的事情,是“小人”所追求的,这与“为己之学”的成德之仁学是有原则区别的。 其二,行仁道即担负起人的道德责任,仁即道德担当。道德践履完全是人之事,在善恶的选择面前,主动权完全操之在人,人是道德实践的主宰。《论语·述而》记:“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注疏》,第95页)行仁道是要实现道德,道德本之于形上之天道,极为幽微深远,似乎对人遥不可及,人不可达至。但事实上绝不是这样,行仁道恰恰是我能决定的事,我要行仁道,仁就来了。《论语·颜渊》记:“颜渊问仁。子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孔安国注:“行善在己,不在人也。”(《论语注疏》,第157页)朱子注:“言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预。”(《四书章句集注》,第132页)为仁完全决定于自己,为仁完全在我,闻义则徙,不待终日,只应当下从自己做起,而不问别人如何,因为道德践履是自己的事,别人是不能代替的。 但在现实中为仁由己绝非易事,它往往需要担当的大勇。《论语·雍也》记:“樊迟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注疏》,第79页)为仁往往面临困难。善恶选择虽操之在人,但人往往不听从善的召唤,而选择恶。因为善恶选择即“义”和“利”的选择,即价值世界和事实世界的选择,“利”的事实世界虽然不能安立人的生命,但它能当下直接满足人作为物的存在的需要,而“义”的价值世界只问人作为价值存在即价值生命能否实现,而不问人的物的存在的功用性满足。虽然从终极来说,“义”和“利”是统一的,但现实的表现“义”和“利”往往是冲突矛盾的,因此,“义”“利”选择、善恶选择往往将人置于困境之中,使人面临道德抉择的痛苦。有时这种道德抉择的冲突甚至能达到极至,而使人面临生死抉择:选择了“义”,或曰选择了“仁”,则失去“生”,即人的生物生命;选择了“生”,保住了人的生物生命的存在,则失去“义”,就会“害仁”。面临此生死抉择,孔子毫不含糊地要求:“志士仁人,无求生而害仁,有杀身而成仁。”(《论语注疏》,第210页)在“义”“利”面前,在善恶面前,在道德世界和事实世界面前,毫无疑问,“义”优先,善优先,道德优先,在任何情况下,即使在死亡面前,人都应优先选择“义”,选择善,选择道德,也即选择“仁”,在这里没有任何的含糊和犹豫,也不容任何的折衷和调和。因为道德是人的存在具有意义的唯一理由,是人之为人的唯一根据,舍此道德,保住此“生”,此“生”只是一生物生命,只是与禽兽无别的一种“物”的存在而已,他作为“人”的存在已经没有了,他是一个真正的“行尸走肉”。相反,保住此道德,守住此“仁”,作为“物”的存在,作为生物生命虽然失去了,但他的价值生命恰恰实现了,他的生命存在的意义恰恰实现了,他获得了人的真正生命——道德生命,他是“虽死犹生”“虽死犹荣”。 因此,“仁者必有勇”(《论语注疏》,第183页),道德践履首先即道德担当,行仁即意味着道德责任,即意味着道德大勇。 其三,仁之践履入手处极为平实而普遍,那就是我们每人都有的“情”。《论语·学而》记:“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注疏》,第3页)这四句话《论语》记为孔子学生有子所说,实际孔子也当说过,正如《研经室集·论仁篇》论证说:“此四句乃孔子语。而‘本立而道生’一句,又古佚《诗》也。又《后汉书·延笃传》云:夫仁人之有孝,犹四体之有心腹,枝叶之有根本也。圣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观延笃以此节十九字与《孝经》十四字同引为孔子之言,愈可见汉人旧说皆以此为孔子之言矣。”“孝”为对父母之情,“弟”为对兄长之情,而“孝弟”为仁之根本,因此,“仁”根本上是从“情”上说的。孔子的其他一些话也证明这一点,如《论语·颜渊》记:“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注疏》,第168页)“爱人”之情,正是仁之情最基本的内容。 “仁”是“情”,“仁”是从人心之“不安”处,从情之不忍处,从情之不容已处开显出来的,来呈现自身的。《论语·阳货》记:“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论语注疏》,第241-242页)宰我问孔子三年之丧之事,他认为为父母守孝三年,使人三年不能为礼为乐,会导致礼坏乐崩。因此,为避免此后果,他建议改为一年。孔子问他:父母死了一年后,还不到三年时,你便吃佳肴,穿华服,你心里安不安呢?宰我回答说:安。对宰我的这种态度,孔子责其为“不仁”。在孔子看来,三年之丧,是天下人的通例。在父母死后的三年中,一个有仁心的君子不会吃美食、听音乐、住华屋,因为这样做,他心里不安,于心不忍。相反,如果象宰我那样,只从功利性、功用性出发,就会否定三年之丧,就会丧失对父母之情,就会心呈麻木,就会不仁。可见三年之丧的合理性,完全存在于人的“情”上,完全存在于人的情之不容已上,你能保住此“情”,就自然认为三年之丧乃是人之当然、应然,就是守住了“义”,就是开显了道德世界,你就是“仁”的;你去掉此“情”,只从功用性的“利”上计算,自然三年之丧不合理,这时你完全沉沦于“物”的生命中,你是“不仁”的。 “情”在古代有两义:一为“实”义,即“真实”之“实”;一为“情感”之“情”。“仁”为“情”之“情”,兼此两义,指直接发之于人内心的、真实的本然情感。孔子又从“直”上指点此义。《论语·公冶长》记:“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论语注疏》,第67页)微生高这个人有“直”的名声,有人向他讨点醋,他家没有,他转而向邻居家讨,再给他。孔子认为,微生高的行为不能叫“直”。孔子为什么这样评判?别人向你讨东西,你没有,出之于本然之情,本之于直接的念头,你会说没有。这时你的心是纯然的、本然的,你的念头是第一的、直接的,你的行为反应完全是应然的、当然的,完全是出于直接的“情”,这时你的行为才是“直”的,也同时是“仁”的,是道德的。但微生高不这样,他不直接说没有,而是转一个弯,再向别人讨了再给他,实际上是微生高的心转了一个弯,他的行为不是出自直接念头,而是出于心意转出的第二个或第三个等等念头,他这时的心已“曲”了,“情”已“曲”了,他的心意和行为已有了目的性:如朱子所言,或为掠美,或为市恩(《四书章句集注》,第82页),或为其他目的,他已完全沉沦于“利”的功利性世界中,已是不仁,已是不道德。 总之,“情”人人都有,乃人本有者,不待习,不待教,人人皆能直情而发,称情而出,因此,“仁”具有普遍性,又具有易简性,人人皆可当下而为,故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注疏》,第95页) 其四,“仁”又是“感通”,是由仁之情的自然感润,而将己、人贯通为一体。《论语》记孔子向子贡讲“仁”,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注疏》,第83页)君子行仁,首先“求诸己”,但仁之情之不容已,必然要求人在尽己之心的同时,由自己推出去,推己及人,由近及远,己立而立人,己达而达人。这种“推”的精神,其实质乃是“感通”,是本之于人的道德的仁心,自然向外感通,由己而感通其他人,从而将己与人、内与外打通,融为一体。此即《系辞》所言“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这种“感通”精神又表现为“忠恕之道”。《论语》记曾子之言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注疏》,第51页)案《周礼·大司徒》:“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郑玄注:“忠,言以中心。”唐贾公彦疏:“如心曰恕,如下从心。中心曰忠,中下从心。”皇侃《论语义疏》引王弼曰:“忠者,情之尽也。恕者,反情以同物者也。”朱子曰:“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四书章句集注》,第72页)可见“忠”和“恕”皆指从人的心上,从人的内在本然之情上,尽己推己,此即“仁”的感通之道。这种仁道的“忠恕”,实际处理的是个人与族群的问题,故孔子多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来指点“仁”:仲弓问“仁”,孔子回答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注疏》,第158页)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执事敬,与人忠。”(《论语注疏》,第178页)当颜渊问“仁”时,孔子更是提出了“天下归仁”的理想社会愿景:“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注疏》,第157页)礼乃本于人情而为之节文,礼的内在根据正是仁,因此若人人能约身反礼,一个仁的道德世界也就实现了。 由上可见,孔子的“仁道”乃是以成就道德人格为目的,是要成就一个道德的世界。它要求人们以无畏的大勇担当起道德责任,以实现自己的道德生命。“仁道”的现实可行性,正在于它从人人皆有的本然情感出发,以个体自己为道德践履的起点,以己之情,尽己推己,自然就能向外感润,而通达别人之情,从而将己和人贯通为一体。而人人都能这样做,人人都这样做,则道德的世界就能实现。 总之,孔子的哲学思想是丰富和深邃的。在人神关系上,他“敬鬼神而远之”,以中和的智慧,将信仰和理性圆融地和谐为一体,将宗教内在地人文化了。在对个人生命的安立上,他通过对“命”的反省,对“义”“利”的分辨,为人类开显出一个道德世界,挺立起人的道德生命,从而解决了人的安身立命的终极关怀问题。在道德生命的达成上,他建立起“仁道”思想,也即道德践履的学说,这一学说要求成就道德人格,实现道德的世界。总的来看,讲求理性和情感的交融和谐,追求道德化和人文化,是孔子哲学的基本特征。 以生命点燃生命 以智慧点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