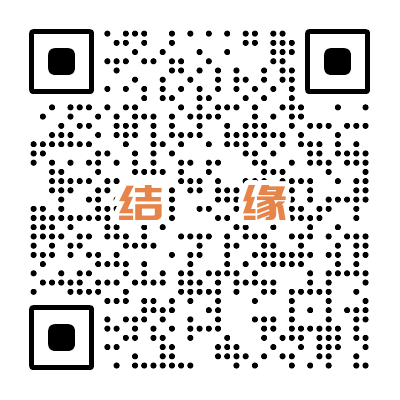刘彬|关于儒家道德哲学的八点认识
01
作者简介
刘彬(1965—),男,字於易,山东滕州人,曲阜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东亚易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孔子文化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周易学会常务理事,山东周易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出土易学文献、《周易》经传、象数易学、儒家哲学,建立《易经》古义研究新体系,正在致力于易图学的挖掘、重构以及易图学派的创立。
02
主要内容
摘要
道德哲学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本文主要讨论了儒家关于道德哲学的八个方面:(一)人成就道德如何有必然性。孟子的性善论充分说明了这种必然性。(二)道德形上学。儒家讲道德从两个方向,一是向上讲到形而上的天道,一是向内讲到人内在超越的心,建立了道德的形而上学。道德非伦理。(三)道德与人伦日用的关系。道德实现于人的生活中,道德的实践在人伦日用中。道德与人伦日用是二而一的关系。(四)道德体悟的本质。道德体悟是情之感,而非智之思。(五)道德体悟如何实现。道德体悟的实现必须经过转识成智。(六)成就道德人格的关键之一——立志。要在现实上成就道德人格,立志是关键之一。(七)道德境界。道德境界是主观的,同时也是客观的,是主、客观的统一。(八)儒家外王的本质。儒家讲外王,其本质是人文化成,是成就一切人的道德价值人格。外王非政治
前言
西方伟大的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年),在其著作《实践理性批判》的“结论”中,曾经写到:
有两种伟大的事物,我们越是经常、越是执着地思索它们,我们心中就越是充满永远新鲜、有增无已的赞叹和敬畏——
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
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
“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即我们平常所说的自然,这其中蕴藏着令人无限沉迷和惊叹的自然法则(宇宙法则)。“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指人能表现出道德行为,在道德行为中,人的无限尊严和价值得以尽情展现,人的光辉和荣光得以尽情焕发。对这两种伟大的事物,人们生发出两大问题:自然(宇宙)法则何以可能?道德法则何以可能?这两大问题,乃是人类理性要处理的终极问题和永恒问题,具有永恒的魅力。作为西方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康德对这两个问题的执着思考,展现于他两部不朽的著作——《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中。
对中国文化来讲,对第二个问题——“我们心中道德法则”何以可能问题的思索,历来是儒家所关注和致力解决的问题。儒学经过了二千多年、三期(先秦原始儒学、宋明新儒学以及现代新儒学)的发展过程,她一直思索、解决的问题都是道德的问题。儒家人物都是道德意识特别强的人,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其他学派有本质的区别。经过历代儒家人物的努力,已经建立起道德学说。这种学说微妙精深,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对世界文明的独特贡献。但这套学问也较难把握,较难理解。本文打算对儒家道德学说的八个方面的问题,谈一下个人的粗浅认识,和大家一起讨论,以深入领会儒家的道德学说。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人成就道德如何有必然性 ——性善
人成就道德如何有必然性,换句话说,人成就善如何有必然性,这是儒学中真正的一个大问题,而儒学也真正讨论和解决了这个问题。为此,我们必须认真地探讨一番。
首先,我们要知道,儒家认为人是一定能成就道德的,人是一定能成就善的。在儒家看来,这是一个肯定的明确的前提性的事实。因此,人是否能够成就善,在儒家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如何在“理”上,即在理论上说明人能够成就善的理由,即要寻求人成就道德、人成就善是如何有必然性的。因此,儒家着重讨论的是人成就善的必然性问题。
具体地说,儒家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和解决,是在它的人性论中。关于人性学说,唐以前儒家大约有四种说法,即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周人世硕、汉董仲舒、扬雄等人的性有善有恶论,汉王充、荀悦和唐韩愈等人的性三品说。按荀子的性恶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人的本性是恶的,其所以能善,是后天经圣人用善来教化,自己人为勉强训练而成。那么,圣人也是人,他的本性也应是恶的,他是如何得到善的,在荀子实在是不能回答的问题。因此,严格地从逻辑上说,荀子的“性恶善伪”是不成立的,因为它不能也无法说明人何以能得到善。荀子的理论,不能给人提供成善的可能性,当然更不能提供人成善的必然性。
性有善有恶论认为,人性有善有恶,顺其善性则成就善,顺其恶性则成就恶。王充《论衡·本性》记载:“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恶性养而致之则恶长。”董仲舒把性比为禾,把善比为米,说:“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以董仲舒来看,性有善之可能,但同时也有恶之可能。扬雄《法言·修身》说:“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善恶混”即人性有善有恶。按性有善有恶论,人有成善的可能性,但没有成善的必然性,因为同时有成恶的可能性。
性三品说,是把整个人类分成三部分,认为这三部分人的性是不同的。王充《论衡·本性》说:“夫中人之性,在所习焉,习善而为善,习恶而为恶也。至于极善极恶,非复在习。……人性有善有恶,犹人才有高有下也,高不可下,下不可高。……余固以孟轲言人性善者,即中人以上也;孙卿言人性恶者,中人以下也;扬雄言人性善恶混者,中人也。”王充是按“才”即人天生的能力的不同,把人分成三等,上等性善,下等性恶,中等可善可恶。荀悦《申鉴·杂言》说:“有三品焉,上下不移其中则人事存焉尔。……曰问其理,曰:性善则无四凶,性恶则无三仁;人无善恶,则文王之教一也,则无周公管蔡;性善情恶,是桀纣无性,而尧舜无情也;性善恶皆浑,是上智怀恶而下愚挟善也,理也未究矣。”韩愈《原性》说:“性也者,与生俱生者也。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
这三种讲法都是形下的讲法,经验的讲法,事实的讲法。而事实、经验的讲法,至多只是提供了人能够成就善的可能性,而不能提供绝对保证性的必然性。
与这些讲法不同,孟子讲“性善”,直承孔子的形上智慧,完全开辟出一个新的理论境界,这是中国人真正的又一次心灵跃升,又一次真正的智慧闪现。对此,孟子是很自觉到这一点的。《孟子·离娄下》记载孟子的话说:“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孟子之前和之时,很多人讲“性”,孟子认为,他们的讲法都是一种“故”的讲法。何为“故”?不好理解。汉人赵歧注解说:“今天下之言性,则以故而已矣。以言其性者,以利为本耳。若杞柳为杯棬,非杞柳之性也。”并没解释何为“故”。托名为宋人孙奭的解释说:“孟子言今夫天下之人有言其性也者,非性之谓也,则事而已矣。盖故者事也,如所谓故旧无大故之故同意。”(《孟子注疏》)可以看到,伪孙奭是以“事”来解释“故”,他这一疏解很重要。朱熹解释说:“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迹,若所谓天下之故者也。利,犹顺也,语其自然之势也。言事物之理,虽若无形而难知,然其发见之已然,则必有迹而易见。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犹所谓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也。然其所谓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势,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矫揉造作而然者也。如人之为恶、水之在山,则非自然之故矣。”(《孟子集注》)观朱熹之意,是认为孟子赞成这种“故”的讲法,这是误解,因为孟子是批评“故”的讲法的。但朱熹指出“故”为“已然之迹”,已经触及这个问题的关键。在这些前贤启发的基础上,我们现在可以很清楚地说明,所谓“事”,所谓“已然之迹”,就是现在所说的“事实”。因此,孟子之外“性”的讲法,都是事实的讲法,都是经验的讲法,而经验和事实只有可能性,只有相对性,在这里,是无法说明人成就善如何有必然性的。
因此,超拔出这些讲法,孟子开辟了一个形上领域,他所说的“性”和“善”都是形而上的,都不是在事实领域中讲的。因此,孟子讲的“性”不是事实,不是“生之谓性”(告子),不是“生之自然之具”“性者质也”(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不是这些事实。他讲的“善”是无对待的绝对,而不是与“恶”相对的“善”,即不是事实。因此,孟子所讲的“性善”一定是形而上的绝对,是人这种存在(从时间上讲包括过去未来一切时间内的人,从空间上讲包括至大无外的宇宙内一切的人)的终极自性,“性善”本身就是一种必然,因此,人成就善就只能是必然,人成就道德是绝对必然的。
是故,我们说孟子讲的性给人提供了真正打通与天道关系的保证,而人性善这一点就完全、充足、必要地保证了向内心打通的正确性。
二、道德不是伦理
——道德形上学
儒家讲的“道德”,一些人认为与一般所说的“伦理”没有区别,我认为这种认识是不对的。
先看“伦”的意思。“伦”有“类”、“道”意,郑玄《礼记·曲礼下》注曰:“伦,犹类也。”《说文》:“伦,道也。”《诗·小雅·正月》:“维号斯言,有伦有脊。”毛传:“伦,道。”《中庸》:“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孔疏:“伦,道也,言人所行之行皆有道理。”“伦”又表示条理、顺序的意思,《书·舜典》“八音克协,无相夺伦”即此意。“伦”又有“顺”意,《广雅·释诂一》:“伦,顺也。”
因此,伦理指人类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必须要遵循、顺从的一些条理、道理,在一个社会中只有大部分人都遵守、顺从这些条理、道理,这个社会才能正常运转和存在。因此“伦理”表示的是社会关系,是客观的社会存在的“理”。这些条理、道理是在个人之外的,人是必须外在地服从的。因此,“伦理”是一个外在的、客观的范畴。在先秦儒家那里,“伦理”即“人伦”,即“五伦”,即《孟子·滕文公上》所言:“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实际上,先秦儒家所说的“伦理”,就是“礼”,就是孔子一直想恢复的“周礼”,那么一套社会规则,那么一些制度习俗。
因此,所谓“伦理”乃是属于现在所谓“社会学”的范畴,是一种社会科学,是一种关于事实的学问,是一种外在的讲法。
而儒家讲的“道德”观念与“伦理”思想不同。讲“道德”一定是哲学的讲法,一定是形而上的讲法,一定是内在的讲法。“道”乃天道,乃形而上的存在,不是一种事实。“德”即“得”,指人得于道者。“道”不可见,不可闻,无实体,但它一定要发用,要呈现,要流行。在人与道的关系上,从道往人说,是“道”发用流行到人身上,即“道”在人身上呈现,从而形成人的“性”,即《中庸》“天命之谓性”。从人往道讲,是人禀受了“道”,是人得到了“道”,是人以“性”去实现“道”,即《中庸》“率性之谓道”。
因此,讲“道德”一定要向两个方向走,一是要向上走。要突破人被定位在“社会”这个层面上的局限,要往上走,要在“宇宙”这个“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大全”中找到“人”的位置,要打通“人”与“天”的通道,要打通人与宇宙“本体”的通道,要从“社会的人”走向“宇宙的人”,要找到人的“宇宙价值”。实际上,这是从“有限”(被限制)走向“无限”(对“限制”的突破)。
第二是要向内走。向上走不是向外走,不是要认识宇宙间的一切事物,了解宇宙的一切知识,不是这些广度的问题,不是“知识”(现代人说的意义上)的问题。而是要把向外的眼光收回来,向人自身转,向人自己转,向人的内心走去,向内走。“道”这个“本体”落实到人身上,也就是说,“道”本来就在人身上,“人”本来就与“道”合一。但人不是自然地“觉解”这个“本体”,不是直接地“知解”这个“道”。人身这个形体,绝大部分都是一团黑暗,都是与“道体”隔绝不通的麻木的存在。只有人的“心”是一个管道,是一个通道,只有从这个管道、这个通道,人才能“接上”与“道体”的关系,人才能“觉解”道体。反过来,“道体”也只有通过这个管道,才能“呈现”出来,才能把自己呈现于人。因此,人的“心”虽然是人身上可怜的那么一点,那么一块“方寸之地”,但万万幸的是,这一点是一个“知觉灵明处”,是有觉解的,是神灵的,而不是麻木的;是明朗的,而不是黑暗的;是能感通的,而不是隔绝的。因此,人只有通过、只有借助“人心”,才能觉解“道德”,才能实现“道德”。对人来说,人要成为“德性”的存在,“人心”是唯一的可能。所以,儒家讲“道德”,讲“君子之学”为“为己之学”(孔子),讲“求放心”,讲“反身而诚”(孟子),讲“返求内心”,讲“方寸之间,森然万物”(朱熹),讲“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陆象山),讲“致吾心之良知”(王阳明),等等,都是向内讲,向内心上讲。实际上,也只能这样讲,也只有这一种讲法。
因此,“向上讲”就是“向内讲”,“向内讲”就是“向上讲”,二者是统一的,是一回事。儒家的这两种讲法,实际上是一种讲法,“两种讲法”只是我们的一种方便说法而已。
由此可见,儒家讲的“道德”是绝对不与一般讲的“伦理”的意思等同的,二者是有原则区别的。简要地说,“道德”是哲学的讲法,是内在的讲法,“道德”提供给人的是一种“彗解”,其目的是要成就人的德性生命,达成人的生命价值。从实质上讲,“道德”因为是形而上,是不能“讲”的,“尊德性”是生命体验,是生命的实现,“讲道德”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生活”本身,就是我们的生命过程本身。所谓“讲”,只是由一个先知先觉者(古代所谓“圣人”,如孔子等人)向我们这些人,提供一个更好地了悟“道体”的契机罢了。因此,“道德”不是学问,不是知识。如果照一般说法,说“道德”是一种“学问”的话,也只能说“道德”是性命之学。而“伦理”是外在事实之理,是外在知识,需要分析、学习和掌握,是正式的现代所说的“社会科学”。
三、“道德”与“人伦日用”
的关系
——二而一
讲道德的实现又要向下讲,向外讲。向下讲,是说形上的道德必须在形下的人伦日用中实现自己,落实自己。《易传·系辞》讲“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之道必须在形而下之器中实现自身,因为形而下之器是形而上之道实现自身的唯一凭借。没有这一器的凭借,道只能成为真正的虚无,即不存在,或曰其存在只能落空。“人伦日用”就是形而下之器,没有人伦日用,道德就只能永远落空而不能实现。而道德必须实现,这是道德的本性,不能实现就不是道德,没有现实性就不是道德。这一切决定了道德只能借人伦日用、就人伦日用、不离(即“即”的意思,“即”是“不是”而“不离”的意思)人伦日用而实现自身,因此,讲道德又一定要向下讲。
同时,讲道德又要向外讲。“向外讲”是指由心内向心外讲。道德体悟不是只在自己心里就能“思”到了,在自己心里就能“觉悟”到了,只在自己心里就能达到“道德境界”了。不是这样的。首先道德问题是在生活之“事”中必然产生的,也是生活本身要求它必须解决的,因此道德问题的产生和解决是依赖于外在之“事”的,并一定对外在之“事”产生了作用,才从而达成“道德境界”的。这涉及到主体之“心”和客体之“事”的相互作用、相互达成的动态关系问题,也就是“内”与“外”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哲学讲这叫“内外交相成”,在内与外的相互作用中,“内”依赖于“外”而成,“外”依赖于“内”而成。在主体和客体的“内外交相成”中,达成主客合一的“道德境界”。
因此,儒家讲“道德”,是向上讲,同时向下讲;向内讲,同时向外讲,是彻上彻下、彻内彻外,是上下合一、内外一体。实际上,上下、内外的区分只是一种方便的说法,只是一种逻辑上的做法,实际道德和人伦日用是一体的。
四、“道德体悟”的本质
——“情之感”而非“智之思”
从人类认识的方面讲,道德体悟也是一种认识活动,但这种认识活动与知识的认识活动不同。知识是怎么来的?是通过“智之思”来的。“思”的特点是分析。所谓“分析”,是指人借助于他的理性思维方式,将很多事物在他的“头脑”中“分割剖解”,找出、“抽象”出共同属性。而知识是如何形成的?康德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按他的说法,知识之所以能形成,是人以先验的时间、空间形式,和先天的十二个知性范畴(具体讲,包括量的范畴、质的范畴、关系的范畴和样式的范畴,如统一、多样、整体为量的范畴,实在、否定、限制为质的范畴,原因和结果、实体与属性、作用和反作用为关系的范畴,可能与不可能、存在与非存在、必然或偶然为样式的范畴),对感性材料进行整理加工的结果。(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这些都属于“智之思”的知识活动,是一种只在人“大脑”中进行的逻辑活动。是一种“思的活动”,是一种逻辑的思维活动,是外在于生活实践本身,而可只在人头脑中进行的“专门的认识活动”。
但问题是“道德体悟”活动不是“智之思”,不是分析活动,不是逻辑活动,不是知识活动。这涉及到“体悟”特质或曰特性问题。“体悟”的特质是什么呢?“体悟”是人之“情”的“感”,是“感”而“通”。儒家用两个字把这个意思讲透了,一个是“仁”字,一个是“义”字。何为“仁”?孔子用“仁”这个字来点化人人所本有的恻怛、恻隐、不忍的情,此情发动,自然就能“感”,而“感”就是一种“贯通”和“打通”,就是“上接天道”“贯通天道”,就是人“德(得)道”了,就是所谓“体悟道德”了。而此情“感通天道”,“天道”当下就实现自身,呈现自身,就向人发布“命令”。康德把这种天道命令称为“绝对命令”,它是一种无条件的、绝对的命令。就人来说,就自然听从这种“命令”,就自然发为当时、当下合适、合宜的行为,这就是“义”了,故古人把“义”解释为“宜”,“宜”就是当时、当下应该怎样就怎样,就是应然,就是应当。康德把这种行为称为“义务”。这种当时当下应该如何做的“义”,这种行为方式的应当、应该,不是通过“思”而获得的,不是通过“分析”而获得的,不是知识性的指导,而完全是当时当下主体人所贯通的“道”的自然的发用流行,是当时当下主体的人的“无思”“无为”的行为。
这种“情之感”的特性也决定了“体悟”的另一特点,即“悟”一定是“顿悟”,而“智之思”实质上一定是“渐”的,这也把二者区别开来。对“顿悟”,禅宗有很好的说明。禅宗人说悟“如桶底子脱”,桶底子脱,则桶中所有之物均一时脱出。“悟”一定是“全悟”,否则就不是“悟”,不能说“悟一半”、“悟三分之一”、“悟四分之一”等等。故“悟”一定是“一下子悟”,“悟”之前不是悟,“悟”一定是个“一”,否则就是个“零”。这是因为“道”只能是个“一”,只能是个整体,只能是个“大全”,而不可分割,不可“分析”(不可在大脑中,用逻辑的方法把它分割开),对它的认识活动“悟”当然也只能是“一下子”了。而“智之思”的知识活动如桶中拿东西,拿了一些东西,还有东西,还可继续拿。故“智之思”所要认识的“理”,是个“二”,一部分“理”被认识了,一部分“理”还没被认识,可再继续认识。因为“理”是可分割的,是可分析的,有整体与部分之别,有部分与部分之别。故“智之思”的活动一定是个“渐”,是由一部分到另一部分,由部分到全体。用逻辑的话说,是“分析”,或由“分析”到“综合”。
道德的实现不离人伦日用而达成,但大部分的人伦日用活动达不成道德行为,道德的实现实际上是非常之难的,以颜子之悟也只能“三月不违仁”。故道德活动是人的一种高级的实践活动,绝大部分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觉悟”过一回道德,可能只有极少数的“上智”者在某一时点上“觉悟”过,达成过“道德境界”。
五、道德体悟如何实现
——转识成智
体悟道德如此之玄,能否真的发生和实现?很多人对此心存疑虑。实际上这里确实涉及到一个关键问题,对此问题古人也经深入思考,提出了“转识成智”的说法。“知识”是一种“识”,要想实现“智”即“智慧”,要有一个“转”,即“转路子”、“转方向”、“转化超越”,这是一种内容、方法的大转换、大提升,是一种质的飞跃。正如人言“百尺竿头,再上一步”,竿子共一百尺,已爬到第一百尺,怎么再上?但一定是能上,只是要“超越”,要“质的转换”,沿着原来的路子不行了。
讲到这里,还是不能回答人为什么能实现“转”?实际上这种能够“转”的“实现原理”就在人的“心”上。人的“心”,有两种功能:一种是逻辑的、知性的“知”,可称为“为学”(老子的话),或称为“思”。这种活动,是由主体追求客体,并有所“得”而成的,这时人的心一定要“有为”,要“为学”,要追求。另一种是“直觉”的“体证”,按宋明儒的说法叫“逆觉体证”。什么叫“证”?“证”是“证明”,是自己把自己摆在那里,让别人看得见,看的明。“证”是客体之“道”自己把自己摆在人的“心”上,自己把自己在主体的人的心上实现出来,呈现出来,是客体到主体的身上去落实自己、实现自己。这时人这个主体完全不用去追求客体,也完全不能追求,人心完全是“无为”的,是“无思”的,一毫之力也不费,只可以、也只能“以神遇”,“直直接接”“觉”到了“道”,并“体现”出来“道”,这就是“体悟”。故体悟道德,绝对不是只在头脑中穷索力探,极尽思维、思想,所能“思”“想”出来的。“体悟”,它是生命本身的“天机开张”,是生命本真的“灵光乍现”。它完全是生命之事,完全是生活之事。换言之,生命自身自有“体悟”,生活自身自有“直觉”。而“思”“想”这个小小的区域,只能为人的“体悟”提供一种契机,即“缘”,而它本身是不存在“体悟”的。首先投入生活吧,一心一意地去“生活”,在“生”的这种“实存”中,真真正正感着,痛着,乐着,愤慨着,感激着,绝望着,希望着,奋斗着,挣扎着……在生命的某一刹那,你可能直觉到那种生命本身的“天机开张”,生命本真的“灵光乍现”。因此,“体悟”是人的生命实感的事,不是纯思的事。
六、成就道德人格(价值人格)
关键之一
——立志
儒家思想的独特贡献处,是开拓出一个道德世界即价值世界,她的目的是要成就道德人格即价值人格。她用的词,如“士”、“君子”、“贤人”、“圣人”等,在核心的意义上,都是价值意义的,表示的是人格的价值等级。“价值”与“事实”是对列的,是不同的。人的能力、才分是“事实”之事,不是“价值”之事。价值之人格,人人皆可成就,皆可实现,不论是愚笨的或聪明的、贫贱的或富贵的、做恶的或行善的、中国的或外国的、过去的或未来的或现在的,等等,只要是人,他皆可成就道德,成就价值人格。故儒家讲价值之人格,是囊括时空、面向一切人讲的,是具有最大之普遍性。她在理论上肯定人人皆可成圣人,如孔子说“吾欲仁,仁斯至矣”,但没有肯定在现实上人人皆成圣人,如孔子说成仁极难,孔子认为能称为“仁人”的只寥寥二三人而已。
为什么在理论上人人皆“可”成为圣人,而在现实上又不能人人皆称为圣人?此无他,在能“立志”与不能“立志”尔。盖“立志”是儒家生命学问的起始,是成就价值人格的基点和起点。在“志”上,在“志”能不能“立”上,一个人能跃升价值世界、还是永远沉沦于事实世界,就于此判分两途了。看孔子人格的炼造,起始于什么呢?“吾十五而志于学”,正在“志”上。此“志”此“学”,在根本的意义上,不是要去学习很多知识,不是要去增长自己的能力,(这并不是说孔子的“学”就没有学习知识、增长能力的意思,有这些意思,但这些意思一定是第二位或第三位的,不是根本的)而是“志于道”,志于成就价值人格,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所谓“志士仁人”,把“士”称为“志士”,皆应如此看。曾子言:“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孟子言:“士尚志。”荀子《劝学篇》言:“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其言皆有儒家精义,宜细玩味之。
因此,一个人只要“立志”,就有可能成就价值人格,换言之,人就有“体悟”之可能(“体悟”即成就价值人格之事)。一个人如不“立志”,他就永远桎梏于事实世界中,永无超越之可能,永无“体悟”之事。看看这个现实世界,绝大部分人不就是毫无“立志”之心,而甘于、乐于沉沦于事实世界中吗?此也不是现在世界如此,过去未来世界皆如此,故世界永如漆黑漆黑之长夜,永如无边无际之巨海,永无光亮和希望。而儒家所提揭开拓的道德价值世界,如一缕微光,如一叶小舟,虽微虽小,但真正给人以光明和希望,真正给世界以希望,真正给人类历史以希望。但以一微光照无边黑夜,以一小舟涉无际之海,此事易否?此事难否?此事有几多可能性?有几多可行性?打一比方,做此事如“以独木撑天”,用“天”这个词也不能尽此意,应说“以独木撑宇宙”,庶几近之。(古人曰“为天地立极”,就是立一根柱子把宇宙撑起来。)故儒家所进行之事业,以常人看是“不可能之事”,但儒家就是要行此“不可能之事”。能行“不可能之事”,方是真儒家。行事求“效果”,求很快能实现,此不是真儒家。故儒家有真正伟大而庄严的“担当”,有真正肃穆庄严的“担当意识”。孔子言:“知其不可而行之”,明明清楚地知道当时当世的“不可能性”,当时当世的“不可行性”,但一定要“行之”,要“行道”。这是一种什么精神?曾子言:“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士”肩膀上担着的是多么重啊,“士”走的路是多么的远啊。把撑起宇宙的一根柱子担在肩膀上,你说重不重呢?这条路一直走到死那一天还没走完,你说远不远呢?故儒家“志”不在一时,而在万世;不在一国,而在天下。(故儒家讲“平天下”)
故对儒家所讲的价值世界、价值人格的深远的意义,我们不可轻轻掠过,而应体味再体味。
七、道德境界
——主客观的统一
从道理上分析,人进行道德活动有两个层面:一是体悟道德,即觉解。二是体验道德,更准确地讲是“体现”道,即道德在人身上获得实现。在实际的行为中这两个层面是一体的,所谓“觉解道德”,不是抛开生活,专门进行“思”,而是即生活的“事件”本身中,感受到道德向人的呈现。因此儒家讲的道德的形上学绝不是纯粹的一种思,不是一种纯粹的哲学活动,不是一种纯粹的学术活动,不是分析研究一种知识,而是一种生命的问学,是生活实践本身,是生活本身。实际上,人除了“活着”,除了“生活着”,除了“生命存在着”这个事实之外,这个过程之外,就没有什么了。因此,人的道德活动也只有在生活本身中,即生活本身,扎根于生活本身去做,这是唯一的可能,是唯一的必然,是唯一的必要。
道德活动是生活本身,因此道德行为一定是要客观化的。儒家讲的“道德的境界”,绝对不仅仅是一种主观的东西,不是说我只是通过“思”,就在我的“头脑”中,在我的“心中”,就“觉解”道德了,就达到了“道德境界”了。儒家讲的“境界”不是这个意思。“境界”这个词,不是现在一般人所了解的意思。对此,牟宗三先生有很好的说明。“境界”这个词在先秦典籍中没有,是后来佛教新创的名词。“境”是指着对象讲的,是指外在的对象。按佛教的解释,“界”是因义,是ground或cause的意思,是原因的因,是根据的意思。有这个因,就可以决定一个范围,就可以成为一个界。后来唯识宗讲“境不离识”,把外在对象拉进来,把它主观化。因此,“境”又有表示主观的意思。(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由此看来,“境”这个词兼表客观和主观,是主客观的合一。“境界”也是这个意思。儒家的“道德境界”就是表示主观和客观的两个层面的合一。说某人达到“道德境界”,是说在这个人的主观心境上体悟到道德,同时在外在客观行为上实现道德,在生活行为上实现道德。
八、儒家“外王”的本质
——外王非政治
人们常讲,儒学一言以蔽之,即“内圣外王”之学。实际上“内圣外王”,本来不是形容儒家思想的一个词,它最早出现于《庄子·天下篇》中。《天下篇》作者认为古代的道是一个整全,这种道可称为“内圣外王之道”。后来此“道”破裂,诸子各家各得其偏,只不过“邹鲁之士”的儒家得到的更多一点。后来人们用“内圣外王”来概括儒家的思想内容,也可以,也得到了后人的认同。在先秦儒家那里,其思想包括两部分,即“仁”的部分和“礼”的部分,如用“内圣外王”这个词,其“仁”的部分可称为“内圣”,其“礼”的部分可称为“外王”。孔子所讲的“礼”,儒家(特别是先秦儒家)所讲的“礼”,不是人们一般所理解的“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规范”的意思。如果我们仔细、深入读《礼记》,就会理解孔子等人所说的“礼”不同于原来周公所制定的、用来“秩序”社会、人们必须执行的那么一套“社会规范”。在孔子手里,“礼”被他“意义内涵”地改造了,被他“理论层次”地提升了,“礼”已经超越出“社会规范”的层面和意义,而成为成就“价值人格”的手段,从而上升到“价值”层面和“文化”层面,也即“人文化成”的层面。因此,我们说孔子的“外王”是“人文化成”的意思。
后来孟子讲“仁政”“王道”。依孟子意思,所谓“仁政”“王道”意思很简单,即君主的一切政治行为所依凭的标准是“民心所归”或曰“民心所向”,而“民心所归”“民心所向”是“天意”的表现,即“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我们要注意,“天”在孟子那里是“义理”层面的,即“义理之天”,用现在的话讲,是“价值意义的天”。因此,孟子的“王道”是“价值意义”的,绝不是社会意义的,绝不是“政治意义”的。
现在的“政治学”也讲“要顺从民心”“要合民意”,从表面上看和孟子讲的“仁政王道”意思似乎一样,但实际上完全不同。我们要注意,政治学所讲的“民心”“民意”是指“人民的共同的欲心和欲意”,是人作为“生物意义”上的需要,是“事实层面”的,而绝不是“价值层面”的。因此,不要把这两个层面的意思混淆。“仁政王道”是“价值意义”上的,而“价值意义”的根本目的,是成就“价值人格”。从内容和手段上看,“仁政王道”和“人文化成”有所不同:前者直接从“仁心”上入手,这是一种“先立其大”的“简易”工夫,这适用于“上智”者;而“人文化成”则从外在的“礼文”入手,由外到内,最后在“心”上“化”之,这适用于一般人。但二者最后达到的目的完全一样,都是成就价值人格的,而不是培养一个“遵守社会秩序”的“顺民”,这一点是肯定的。
儒家所成就的非个人人格,而是“群体”人格。孔子讲“仁”,“仁”为成就价值人格的核心,而“仁”正为“人之不容已”,正为“人之真情不能停止的感通”,正为“人之真情不能停止的感润”,“感”而向外“通”,由“通”到亲人这里,“通”到别人那里,从而连属亲人和别人、家国天下为一体。故“仁”本身即为成就一切人人格之意。孟子讲的“推”,也完全是此意。儒家讲的“人格”,本不仅是“自己的个人人格”的意思,更根本的含义上是成就“一切人”的价值人格的意思。儒家讲的“平天下”,乃是“文化之平”,即“人文化成天下一切人”之意,即以“仁心”感通一切人,以“礼义”感润一切人,使之变化气质,“化”掉他们“气质事实”中的“执着”,由执著于事实之“利”,而超拔出来,而听从于价值之当然的“义”,而“成就”“达成”价值人格。《易传·彖传》解《咸》卦说:“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正彰显儒家大义,需深体会之。
故儒家的“外王”之意,只能从这个地方看,只能从“人文化成”这个地方看,只能从“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这个地方看。儒家所从事的“外王”“平天下”的大业,是引导一切人从所时时遵从、践履的“外在礼文”上,来契会其背后的、内在的、超越的“当然之义理”,此“当然之义理”乃上通于天道,从而在人的身上把“外在的礼文”和“内在超越的义理”贯通起来,并实现于人的生活中。这时,可以说就成就价值人格了。如果天下一切人都达成这种人格,一切人都“平齐”地实现了价值人格(在事实层面上,人是不能齐平的,庄子所谓“不齐,乃物之情”精辟地表达了此意。只有在价值层面上,人才能是真正的“齐平”),那就是“平天下”了。
故儒家的“外王”,实乃超越了政治。儒家并没有、也不打算正面地、正式地讨论“政治”,而是“跳过政治”或曰“滑过政治”。如以“政治”或“政治哲学”等等来界定儒家的“外王”,实是小视了儒家的襟怀和学问大义,也没有看到儒家学问所面对的层面和它的严重不足和严重后果。“政治”乃属“社会学”的范畴,它所处理的是“社会”层面的“事实”,其中最核心者是“权利事实”。“秩序”不是政治的核心义。儒家不讨论“权利事实”,没有开出“政治的学问”。儒家所讲的“礼乐”,不是政治层面的含义,而是“文化”层面的含义,是“人文化成”的含义,后人理解“礼乐”为“政治”,这是误解。“政治”讨论的是权利的取得、分配以及运行的问题,是社会的形成、运行的问题。儒家不讨论此问题,先秦其他各家都不讨论此问题。他们都滑过了这一事实的、但对人们的实际生活又切实重要的问题,故在中国文化中没有开出“政治的学问”,其严重后果是没有形成“政治社会”或曰“社会”,没有形成“市民社会”。故中国人从没有“社会意识”,没有“国(state)的意识”。儒家只有“文化”意义上的“天下意识”,没有“国的意识”。故中国在“社会”的发育上,是一个婴儿,是在婴儿阶段发育就停止了,是严重的残缺。
从人类文明的视野看,到现在为止人类文明发展出了两步:第一步解决人的事实的存在的问题,即人作为一个事实的存在者,他如何保住这种存在。这一步包括要解决物质生存资料和社会存在问题。第二步解决人的价值存在问题,即意义存在问题。中国文明在第一步上一下子就轻轻地滑过去了,就“超越”了第一步,就跳到第二步上,并紧紧地抱住第二步,在这块田地里精耕细作,种出了美丽的花。故第一步文明发育严重不足,第二步文明早熟,这是中国文明的特点,有其优,也有其严重的缺陷。她代表了人类的高层次文明,是人类未来的文明内容。但她恰恰没有解决好当下、现实的问题。曾有人言:中国文化,救中国而不足,但救世界而有余。是有道理的。西方文明紧紧啃住第一步,穷探力索,扎扎实实地开出了事实的学问,开出了科学和民主,真正形成了“国家”,形成了社会。而在第二步上则不足。两相比较,都有各自的问题。中国文明过分早熟,是不正常的,不是健康的状态,故在第一步上出大问题,出严重的问题。如中华文明五千年,可到现在物质生存的问题远远没解决,“社会”远远还没形成,人们到现在不会过社会生活。故我们必须吸收西方的第一步的成果,把科学和民主这种理性精神拿过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实际上中国人还远远没有形成理性精神,理性精神还远远地发育不足。故我们要正视这一问题,要解决它。
以生命点燃生命 以智慧点燃智慧